在H市郊外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新上任的刑侦队长和警长展开调查。他们很快发现死者是一位社会公众人物--女劳模关红英。随着调查的进展他们发现关红英的生活出乎意料的具有双重性,她一方面以良好的社会公众人物现象出现在公共场合,一方面又过着隐秘的孤独与堕落的腐败生活,杀人嫌疑是一个干部子弟,某杂志社的摄影编辑吴晓明,吴晓明借着给名人拍照的机会,与很多女性关系暖味,关红英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受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颓废,堕落,假扮夫妻出外旅游,甚至在一起拍摄了很多色情性质的照片。关红基做了吴晓明的情人,原本是希望有一日成为吴晓明的合法妻子,但是吴晓明却根本不当回事,而且还不断另寻新欢。当关红项把吴晓明拍摄的色情照片藏起来,试图要挟对方时,吴晓明孤注一掷,将她杀害了。<br> 《红英之死》是作者裘小龙的长篇处女作,2000年在美国出版后,备受好评,先是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大奖和白芮推理小说奖,尔后获得安东尼小说奖,即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纽约《新闻日报》将它评选为2000年最佳十部作品之一;已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家翻译出版。<br> <br>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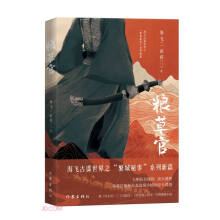



想起来,还真是绕了一个大圈,颇充满了反嘲的意义。窗外,众多的新建筑群一片灯光灿烂,仿佛与我相互纳闷地乏眼。十五年前,在这栋宾馆的原址上,好像是一所街道保健医院,记不太清了,不过我还确实记得,当时我正在赶译一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译稿后来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部集子中。1988年,我一点儿都没想到自己后来会用英文写作,写推理小说。而且得了推理小说的国际大奖,翻译成十多国文字,还正由人翻译成中文。
这几年在美国读书界,读者们问我问得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一个原来用中文写诗、译诗的人.怎么会用英文写起了小说?
通常有一个简单的回答。阴错阳差,生活中,往往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出另一件,再导致另一件,因果之链一环扣着一环,在最终的结果中再难辨认出最初的起因。
还有一个也相当机械化了的回答。九十年代中期后有机会经常回国,目睹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觉得作为个人抒情的诗很难对此描述,转而尝试其他的文类,试着在我已习惯了英文电脑上写,由于我以前没有写过小说,推理小说为我提供了一个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现成框架,可以在里面写入我想说的一切。
不过,还有一个在那儿不太经常作的回答。在西方,对中国的介绍好像总有一些倾向,在时间上要么是三十年代,要么是文化大革命,至于人物,一般都是偏僻乡间的农民,或充满悲剧色彩的红卫兵,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有一次看完电影,听一个美国朋友问我,你们中国人是否在做爱的夜晚都要在窗口挂大红灯笼,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因此我想写一部关于当代中国的书,背景放在中国的某个大都市,时间安排在九十年代,作品里面的主人公不同于西方读者所习惯看到的,而是受过高等教育,写现代诗,也会外语,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也多少触及到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一些深层文化问题。我这样写,并非故意要去作什么反东方主义的尝试,只是想尽可能客观地写我自己所熟悉的一切。
当然,从新批评主义的角度说,这很可能只是作者的意图缪误(!ntentjOnaifallacy),作者自以为要在作品中说些什么,其实并不是作品真正所说的。这也涉及到读者反应,即不同的读者会在作品中读到不同的东西。因此,一个法国的批评家说他在其中看到了中国的美食传统:芝加哥论坛上的一篇书评认为作品涉及到语言怎样拯救灵魂的问题;一个意大利的研究者声称在书中看到了艾略特在中国的境遇.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则在一个捧着ViSLja0 Basic买大碗茶的小姑娘身上发现时代的反嘲,而Anrmett日ubinStein,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我在国内读研究生就读过她文学史专著)给我写信说,作品对当代中国的刻画,还算是“不偏不倚”。
不管怎样,读者反映或批评不是由我来做的;意图谬误或否,在国外写中国,我还要面对一个假设读者的问题(impliedreader),即在写作时必须意识到特定文化读者群的需要。如有些背景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对西方读者来说却会是雾里云里。(这可能也是翻译的中文作品在英美始终不是太畅销的一个缘故吧。)我不可能在文本中解释,只能通过叙述中有意识的处理,通过人物的对话,尤其通过有选择地呈现有关细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身临其境般地理解一个中国的故事。这一点其实不算太难,因为一些细节是我或多或少体验过的,都存在记忆中,自己也乐意一遍遍地回到记忆中去。或许,就像普鲁斯特说过的那样,只有回忆过了,一个人才算真正活过。<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