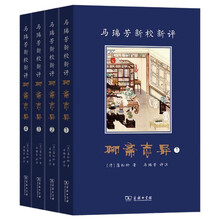夜深了,山间吹来的晚风息了。打谷场上也静了下来。丹尼亚尔靠近我,在草垛脚下躺下来,但过了不多时又爬起来向河边走去。他快到陡岸的沿上停了下来,就那么一个劲儿地站着,倒背着手,将头微微偏在肩上。他背对我站着。他那颀长的、像是用斧头砍削出来的有边有棱的身影,在柔和的月光中显得清清楚楚。他似乎在细细倾听那大河的流水声,——夜晚,河水下滩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可闻了。可能,他还在倾听我所听不见的一些夜的音响和喧嚣。“他又想在河边过夜啦,真是怪人!”我觉得好笑。<br> 丹尼亚尔不久前才来到我们村里。有一天,一个小家伙跑到割草场上说,村里来了一个伤兵,至于是什么人,谁家的,他却不知道。哈,当时可热闹啦!村里有那么一股劲头儿:前方战士要是有人回来,不论老人、小孩,都一齐成群成群地拥去看新来的人,和他握手问好,问他有没有看到自家的亲人,听听新闻。这会儿便响起一阵无法形容的喊叫声,每个人都在猜想:也许是我家哥哥回来了,也许是哪一位亲戚?割草的人们全都跑去,瞧瞧是怎么回事。<br> 原来,丹尼亚尔是我们本地人,本是我们村里的人。老人们说,他在童年便成了孤儿,过了三四年沿门乞讨的生活,后来跑到卡克马克草原哈萨克那里去了,——他的母系亲属是哈萨克。要说该把这孩子找回来,可就没有那样近的亲属,就这样大家把他忘记了。别人问他离家以后怎样生活,丹尼亚尔只回答几句应付应付。可依然能够理解到,他曾经加倍地吞够了生活的苦果,尝尽了孤儿的辛酸。生活驱赶着丹尼亚尔像风卷球一样到处奔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在卡克马克咸土地带牧羊,等长大了,在沙漠里开运河,在新建的国营棉花农场工作,后来在塔什干附近的安格林矿井里工作,打这儿进了军队。<br> 丹尼亚尔回到家乡,人们用赞许的态度迎接他。“不管在异地飘泊多久,现在是回来了,就是说,命定要喝家乡沟里的水。而且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语言,多少带一点哈萨克腔,但仍然说的是地道的家乡话!”<br> “都尔把儿跑遍天涯也要寻找自己的同群。谁又不觉得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人民可亲!你回来,是好样的。我们高兴,你祖先的在天之灵也高兴。感谢真主,但愿打垮德国人,过过太平日子,你也和别人一样,成个家,让你家烟囱上也冒冒烟!”有一个长辈这么说。<br> 提起丹尼亚尔的祖先,他们准确地断定了他是哪一支的。我们村里就这样出现了一个“新族人”——丹尼亚尔。<br> 于是生产队长奥洛兹马特把这位脊背微微向前弯、瘸左腿的高个子士兵,领到我们割草场上来了。他把军大衣搭在肩上,急急忙忙地走着,尽力跟上奥洛兹马特那匹一溜小跑着的矮壮的小牝马。至于队长本人,和颀长的丹尼亚尔在一块儿,他那小个儿,那活泼的姿态,真有点像一只不安生的河鹬。孩子们甚至都笑了起来。<br> 丹尼亚尔受伤的腿还没有痊愈,膝部还不能打弯儿,因此割草他不行,就把他派到我们孩子们这儿来,在割草机上工作。说实话,我们不太喜欢他。首先他那孤僻劲儿,就不合我们的意。丹尼亚尔很少说话,就是说话,也叫人感觉他这会儿在想些别的不相干的事,他有他的心事;而且叫你难以断定,他是不是在看着你,虽然他那一双深思遐想的眼睛直对你脸上望着。 在那个秋天,辍学两年之后,我又进了学校。课后我时常到河边陡岸上去,坐在此时已经空旷无人的当日的打谷场边。我在这里用学生颜料画出自己的第一批素描画。甚至依我那时的看法,我都觉得不够满意。<br> “颜色不行!能有真正的油画颜色就好了!”我对自己说,虽然我还想象不出,真正的油画颜色该是什么样子。<br> 只是在若干年后,我才见到了用铅管装着的真正的油画颜色。<br> 颜色归颜色。可是看起来依然是老师说得对:画画必须学习。谈到学画,过去连想也不敢想,当哥哥们一直杳无音信,妈妈对我这个惟一的儿子,两家的男子汉和养家人,怎么也不肯放手的时候,哪里还能谈到学画?我连提都不敢提。可是秋天就像故意逗弄人似的,显得分外美丽,就等你去画它。<br> 清凉的库尔库列乌河水已经落下去了,浅水处露出水面的顽石上,长满了暗绿色和橙红色的苔藓。光秃的柔情的河柳染过早霜,已变成红色,但是小白杨树却还保留着结实的黄色叶子。<br> 烟熏雨淋的牧马人的帐篷,在河湾里再生草地上显得黑魆魆的,出烟孔上缭绕着一缕缕浓浓的蓝灰色炊烟。瘦长强壮的牡马凄凉地放声长嘶,因为牝马四散回家了,牡马留在马群里,一直留到春天,自然不会安生。山上回来的牲畜,一群一群地在收割后的田地上走来 走去。干枯焦黄的草原上,横七竖八地交叉着印满蹄迹的路径。<br> 很快便吹起了草原风,天空昏暗下来,下起一场一场的冷雨——这是雪的先兆。有一天,是一个差强人意的日子,我来到河上——我真十分欣赏浅滩上那火红的山梨树丛。我在离河滩不远处的河柳丛中坐下来,已是傍晚时候。忽然我看到有两个人,从各方面判断,他们是徒步过河的。这是丹尼亚尔和查密莉雅。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那严峻的、惶惶不安的面孔。丹尼亚尔背着行李包,急匆匆地走着,敞开的军大衣的两襟,碰打着他那破旧的厚油布靴筒。查密莉雅戴着一顶白色浅帽,浅帽这会儿歪到了脑后,身上穿着她最漂亮的那件花衫,这件花衫是她爱穿着在市集上露两下子的,花衫上面罩一件棉绒对襟女褂。她一只手提着一个不大的包袱,另一只手攥着丹尼 亚尔的旅行包的皮带。他们一路在谈着什么事。<br> 他们已经走在直穿休耕地的长满芨芨草的小路上,我望着他们的背影,不知怎么办才好。也许,该喊一声?但是舌头恰似粘在上颚上了。<br> 最后的紫红色的夕照,顺着贴山急行的斑驳的云排滑走了,天立刻黑了下来。丹尼亚尔和查密莉雅头也不回地朝小站的方向走去。<br> 他们的头在芨芨草丛里又晃了两三次,随后就不见了。<br> “查密莉雅……雅……雅!”我使足所有的力气喊。<br> “雅……雅……雅……雅!”到处响起回声。<br> “查密莉雅……雅……雅!”我又喊了一次,然后不顾一切地跑进水里,过河去追赶他们。<br> 冰冷的水花,大片大片地飞到我的脸上,衣服湿透了,可我还是急不择路地往前跑,突然碰到一点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我躺在地上,没有抬头,我泪流满面。似乎黑暗来到了我的头上。芨芨草的秆儿尖细而忧郁地叫啸着。<br> “查密莉雅!查密莉雅!”我咽着眼泪,呜呜地哭着。<br> 我和我最亲最爱的两个人告别了。只是这会儿躺在地上的时候,我忽然理解到,我在爱查密莉雅。是的,这是我初次的、依然是孩子的爱情。<br> 我将头埋到湿漉漉的臂肘中躺了很久。我不仅告别了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也告别了我的童年。<br> 天很快黑了。浓云遮住天空,云层下降到湖面。湖上一片死寂,到处是黑漆漆的。山里像有电焊工人在电焊一样,一会儿银光闪闪,炫人眼目,一会儿电花四散,无影无踪。雷雨临近了。难怪天鹅飞到这儿来过夜。它们预感到在山里会碰到暴风雨。<br> 一声雷响,暴雨倾盆而至。湖上发出轰隆的喧嚣声,湖水激荡着,掀起滚滚巨浪,冲打着堤岸。这是春天的初次雷雨。这也是我们的初夜。雨点打在车上和玻璃窗上,水如泉涌。在漆黑的无边无际的湖面上,闪过几道火红的电光。我们紧紧地偎在一起,小声说着话。我觉得阿谢丽颤抖了一下:或者是被吓住了,或者是冷了。我用自己的衣服给她盖上,把她搂得更紧,感到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巨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多的柔情;我过去也不知道,保护和关怀别人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我永远不让你受任何人的欺侮!……”<br> 雷雨迅速过去了,就像它迅速来到时一样。但是在饱受惊扰的湖面上仍然余波未平,下着稀疏小雨。<br> 我取出在路上用的小收音机。这是我在当时所有的惟一的珍贵财富。我拨好波长,对准电台。现在我还记得,那时正在转播城内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巧伴》。在群山的那面给我们送来了音乐,温柔而强有力的音乐,就像这个舞剧里所描述的爱情那样。剧场里响起了雷动的掌声,人们高呼演员的名字,可能还向他们脚前投掷鲜花,但是我想,剧场里的任何人都没有体会到我们在愤怒的伊塞克湖畔所体会到的那种狂喜和激动。这出芭蕾舞剧是在讲述我们,讲述我们的爱情。那个去寻找自己幸福的姑娘巧伴的命运强烈地激动着我们的心。我的巧伴,我的晨星同我在一起。午夜,她伏在我的肩上睡着了,我久久不能平静,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听着伊塞克湖深处沉重的呼吸声。<br> 早晨,我们回到车场。我受到好一顿申斥。可是当他们知道我这样做的原因后,就原谅了我。后来他们想起我从起重机的机臂下溜跑的情景,还笑了我很久。<br> 我随即起程到中国去。我把阿谢丽带在身边。我打算在半路上把她托给我的朋友阿利别克照料。他的家住在纳伦附近的转运站,离国境线不远。我路过的时候常去看望他们。阿利别克的妻子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我很尊敬她。 <br> 我们出发了。第一件事是在沿路一家商店里给阿谢丽买几件衣服。她当时只穿了一件连衣裙。除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给她买了一条颜色鲜艳的大头巾。她戴上非常合适。路上我们碰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司机,我们车场的老前辈,名叫乌尔马特。他老远就向我们打手势,叫我们停下来。我刹住车。我们走下车,互相招呼:<br> “乌尔马特,您好!”<br> “你好,伊利亚斯。把你手上的那只鹰拴紧些!”他按照当地风俗,向我表示祝贺:“愿老天爷赐给你幸福和孩子!”<br> “谢谢您!乌尔马特。您从哪儿知道的?”我诧异地问。<br> “呃,我的孩子,好事传千里。这条路上一个传一个……”<br> “原来这样!”我更奇怪了。 <br> 我们站在路上说着话,乌尔马特甚至没有到我车前看看阿谢丽。很好,阿谢丽猜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就把头巾蒙在头上,遮掩着脸。这时乌尔马特满意地笑了。 <br> “这就合乎风俗了!”他说,“姑娘,谢谢你对我的尊敬。从现在起你是我们的儿媳妇了,是车场全体老前辈的儿媳妇了。伊利亚斯,收下,这是见面礼厂他拿出钱来给我。我不能拒绝,否则就会使他难堪。<br> 我们分了手。阿谢丽没有摘下头巾。在遇到熟识的司机的时候,阿谢丽坐在车子里,羞答答地用头巾遮住脸,就像在正规的吉尔吉斯家庭里一样。而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们就笑了。<br> 我觉得阿谢丽戴上头巾更美丽了。<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