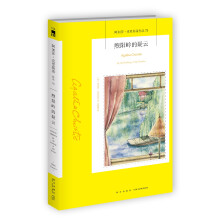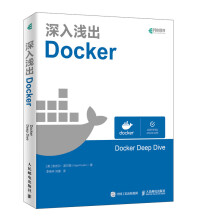薇依一直顽强地寻找自己。所谓寻找,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返回原点。然而,她不是向前走,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结果不断地撕裂自己,使之成为碎片。她只能成为碎片。<br> 譬如她爱,爱使她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可是,当她获悉希特勒入侵布拉格的消息时,便变得不那么和平了。她把投入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当作新的使命。不过,这种转变对她来说是不彻底的。她几乎一直在非暴力与暴力之间摇摆。如果战争非打不可,也就是说,即使出于正当的理由使用暴力,她仍然认为是危险的和卑劣的。至于非暴力,只要有效,便应当在道义上承认它和支持它。她把爱作为一种精神价值进行体认,确信暴力的使用,足以使它荡然无存。人类一旦失去了精神价值,她问:除了卑劣的人,有谁还会去操心政治呢!<br> 当薇依在战争中进入角色,孤绝的气质,随即驱使她投身于暴力行动。在布拉格的学生起义遭到德国人的残酷镇压之后,她同时提出两个行动计划,但都与她个人有关:其一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空投部队和武器的计划”,起草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发动布拉格居民反对占领军,解放俘虏。她向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宣传,并发誓说;如果实施该计划而不让她参加,她将躺到公共汽车轮下自尽!其二,是组建一支活动在火线上的女护士队伍,当然也一定得让她成为其中的一员。结果,两个汁划都没有被采纳。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日后仍然极力寻找机会,奔赴原计划中的慷慨赴死的目标。显然,她试图努力挣脱一种矛盾的处境而终于无法挣脱。<br> 西班牙内战时,薇依面临过同样两难的选择。她不喜欢战争,但是身处巴黎这种近于后方的人们的状态使她更感厌恶。她坐不住了,决定前往西班牙。由于到佛朗哥占领区去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她便带着巴黎工会组织发给她的汜者证,为全国劳动联合会的无政府工会活动分子服务。在战争中,她亲眼看见.红色民兵同法西斯分子一样轻易地杀人,仿佛全然不知道被杀者是有生命似的。梦境被粉碎了。西班牙的罪恶,加深了她在工厂劳动中的受奴役的体验。在人的价值被确立为最高价值,并以此修改她的政治地图的过程中,为战争所展开,为生命所洞见的现实图景对她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地图的每个局部未必因此变得更为精确,甚至有可能大大变形;可是,这一切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其呈示的方位和关系是确当的。你知道,科学的谬误,可以因人性的正确而自行纠正过来。<br> 薇依的政治地图是复杂的。她不断修改。她的地图并没有提供一个类似教科书一样固定的答案,从表面上看来,它是游移的、互否的,实际上,庄严的命意正包含在这种变动之中。<br> 除了战争,阶级斗争也如此。<br> 你看薇依的定义:“当社会权力机制造成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尊严彻底破灭时,这就是一场屈从者反对发号施令者的永久性斗争。”又是人的尊严问题。很明显,这就偏离了正统的阶级斗争观念了。在她看来,阶级斗争确实有其内在的根据,正如赫拉克利特说的,斗争是生存的条件;但是当它发展成为一种斗争学说时,却蜕变成为某种荒谬的东西、空洞的实体,具体的苦难和抗争被抽象化了。她特别指出,阶级斗争贯穿历史的全部荒谬性,根源在于权力的性质。这个结论是政治学的,也是人类学的。她痛恨权力。<br> 大约在薇依那里,权力总是意味着奴役,因此,她会因所谓“主权”问题而改写“祖国”、“民族”的概念。她说:“国家是一种冷酷而无法让人爱的东西;它残杀并取消所有一切可能成为被爱的东西;因此,人们被迫爱它,是因为只有它。这就是当代人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她极力反对国家崇拜,指出它以祖国的名义,索求绝对的忠诚、全部的奉献、最大的牺牲,事实上是一种根本无爱可言的偶像崇拜。当人们大谈祖国时,就很少谈及正义;一旦祖国背后有国家,正义便在远方。她一再说:“祖国是不够的。”在定义人的时候,她也总是喜欢使用如下公式,即:“人,世界的公民。”<br> 这里说个故事。她曾经在课堂上向中学生说起著名的“诺曼底号”邮船,提问道:“这条船的代价可以造出多少工人住宅?”学生听了很反感,立即反驳说,这条船以它的规模和豪华提高了祖国在国外的威望。这堂课肯定讲不下去了。所谓祖国的威望算什么呢!然而,她遭到了抵制。对于“民族”这个词,她同样不抱好感,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应当取消。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人,惟有她知道这个词以及由它组成的各种词组的含义,那就是:死亡和眼泪。<br> “这块土地/可耻地征服了自身。”她曾经引用古西班牙诗句,说君主如何整体地消化了被征服者,把他们连根拔起;而革命,同样把对王冠俯首称臣的人民锻炼成为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是在民族主权至上的陶醉中进行的。她指责百科全书派的成员是被拔根的知识分子,正在于对民族进步的整体性追求,致使人们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不作任何思考,便全盘接受了这一革命传统。于是,爱国主义的轱辘自然向着国家的方向滚过去了。<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