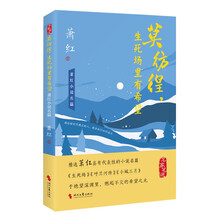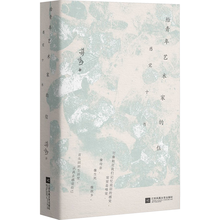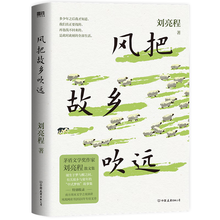纯情莲子<br> 想起莲子,就想起生命中的清纯,那亭亭玉立的荷叶,那雪白脆嫩的莲藕,那一尘不染的莲花,簇拥着纯洁无瑕的莲子,曾在我们所有人的岁月中灿烂。青春无悔,白衣飘飘,洁净如仙的莲子驻留在青葱梦境,偶然还会让人间为之生动如初。<br> “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在瑰丽的南朝,每当想起心中最爱,少女们就出去采莲,抛撒一莲塘的思念如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后面的已经不需赘言,那些欢快的鱼儿和莲叶在迷藏中体味着的,不是幸福是什么?<br> 荷叶和莲花是莲子的初始,那时我为你撑起绿色的荫凉,你为我绽开艳丽的-面容,共同滋润爱情。“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唐朝诗人皇甫松妙笔生花,写出无尽风流。莲花似乎要让人间羡慕。干脆成双成对,合欢并蒂,洋溢着俗世的美好。唐徐彦伯《采莲曲》:“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折藕丝能脆,开花叶正圆。”韦庄认为:“虞舜南巡去不归,二妃相誓死江湄,空留万古香魂在,结作双葩合一枝。”<br> 离离合合的缘分,生生世世的爱情。多情自古伤离别,当莲子的根一一莲藕被我们分离,却仍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如缕。诗人孟郊感叹:“妾心藕中丝,虽断犹牵连。”唐代沈亚之描述:“细绡缕于藕肠兮,差莲跗以齿致。”著名文人温庭筠有《舞人曲》:“藕肠纤缕抽轻春,烟机漠娇娥频。”<br> 莲子也是怜子,一切都是为了你。但莲子的心却是苦的,一片苦心铸情深。唐代李群玉有诗:“莫嫌一点苦,便拟弃莲心。”意思说不能因苦废怜爱之心。金圣叹说,“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是感叹身世。其实,化苦为甜才是人生的正途。据说粤地喜宴,最后一道甜品定是莲子百合,以喻“百年好合、连生贵子”。莲子生汤,或者莲子煮粥,都是凭借着莲子苦心经营,酿造出高贵清洁的精神,养人清心。<br> 纯情莲子被人类发掘自有她的道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此物居山海间,经百年不坏,人得食之,令发黑不老。”《红楼梦》里,元春回贾府省亲,娘家在招待的宴席上有一道“莲子羹”;宝二爷挨打养伤时,吃的也是“莲子羹”。传说有清一代,莲子极为风行,皇后用它护肤,天子用它固精,平民用它“养颜补身”。有说慈禧每隔三五日必服莲子雪耳炖品一次,以祈青春常驻。<br><br> 丝瓜的清趣<br> 小时候,丝瓜蛋汤是母亲的拿手绝活,这道朴质素雅的农家菜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多年之后那些黄黄绿绿清清淡淡还热气腾腾,温暖如斯。岁月如流,情思绵绵,丝瓜无意中牵扯出感慨万千。<br> 丝瓜似乎不愿意承载太多的情意,她只是一味地生长开来。先是攀附他物,一心一意延伸自己的触角,然后,开出朵朵金灿灿的小花,最后,结出一条条碧绿婀娜的丝瓜。虽然努力上进,但默默无闻;即使开花结果,仍然清净儒雅,这就是丝瓜的品格。难怪宋代诗人杜北山要说她:“寂寥篱户入泉声,不见山容亦自清。数日雨睛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br> 清净淡雅:之外,丝瓜还可清心,丝瓜“清热利肠”,可解毒化痰,作汤是消暑的绝佳饮品。据传佛祖释迦牟尼曾用丝瓜藤中所含的液体制成“天罗水”为众生治病,至今仍为佛门所沿用。这种妙自天成的“天罗水”后来被称作“丝瓜露”,可去黑斑,又成为最原始的妇女化妆圣品。在专栏作家古清生眼中,“丝瓜宜于打汤或者清炒,汤是稀释主义情结的澎湃,清炒是散淡心绪的凝结”,深得丝瓜清趣。<br> 飘若出尘的丝瓜,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姿,但竟然成就日本文学中的一个经典传奇,真正莫名其妙。在日本,人们把明治时代著名俳人正冈子规的忌日称为“丝瓜忌”,只是因为他在死前一日曾写出三句有关丝瓜的千古绝唱:“浓痰壅塞命如丝,正值丝瓜初开时。清凉纵如丝瓜汁,难疗喉头一斗痰。前日丝瓜正鲜嫩,忘取清液疗病身。”专家考证,可怜的阿正本来想通过丝瓜汁治理他的肺结核,但终因病入膏肓而不治。<br> 清静无为的丝瓜终于陷入了情网,但其实她从本质上就是多情的,比如她又被叫做恋瓜、思意等等。在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小调里,她和苦瓜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苦恋:“菜园里面一堵墙,苦瓜丝瓜种两厢。郎吃苦瓜苦思妹,妹吃丝瓜思念郎。”到最后,即便老了,不能食用了,丝瓜还把自己奉献出来,做成丝瓜络,仍然忙碌在人类的身边和手边,清洗出一片白净净的天地。<br> 但有得必有失,坊间流传丝瓜能令男人阳痿,还绘声绘色地编排出“丝瓜换韭"的段子,说:“妻令夫买丝瓜,夫立门外候之,有卖韭者至,劝之使买。夫曰:‘要买丝瓜耳。’卖者日:‘丝瓜痿阳,韭菜兴阳,如何兴阳的不买,倒去买痿阳的?’妻闻之,高声唤日:‘丝瓜等不来,就买了韭菜罢。’”但科技证明,此说纯属虚构。<br><br> 快乐开心果<br> 开心杲是呆子中的小调皮,只有她才敢把快乐写在脸上。她在自己开开心心的同时,做一些插科打诨的雅事,弄出一点小小的动静,给色彩缤纷的瓜果世界平添许多喜气。在越来越紧张的现代社会,我们都是开心杲的忠实拥趸。<br> 早就笑得脸变了形,轻轻一掰,便露出自己香喷喷的内心,干净,直白,一目了然。如此夸张的快乐,确实有些猝不及防。这是对人类虚伪的嘲笑。美国华裔著名作家董鼎山先生曾说过一个小故事:某年,一位伊朗诗人想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就运来十八箱开心杲,分赠瑞典皇家学院十八名委员,结果提名无效。小小开心杲,一不小心亲历了人类的一个小丑剧。她怎会不开心?<br> 开心果的波斯名字叫阿月浑子,听起来像是一个不怎么高明的日本女人的名字。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述:“胡榛子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子,二年阿月。”意思好像是说一棵树上结出了两种呆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沿用这一说法,不过将其变成了“阿月浑子”。李殉的《海药本草》则更确切地写道:“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这种叫法一用千年,直到晚近才被越来越不快活的人们称为开心果。真是难为她了。<br> 谈到她如今的名字却丝毫没有传奇色彩。据说她原本快乐地生活在中东圣地的沙漠高地上,果实成熟后会自然裂开,看上去好像人类开心的笑容,所以后来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开心呆”。一种说法是,情侣们如果能在洒满月色的晚上听到开心呆壳爆裂的声音,他们便会好运当头,快乐一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