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了,叫人很难相信。那还是昨天、前天的事,你还在那样地诉说,那样地呻吟,那样地呼叫,那样地恳求,那样地叮嘱,那样地示意;你的容忍,你的愁苦,你的牵挂……一切都是那么活生生的,在这个世界上就这样抹去了?世界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如果有,我倒略可安慰。可是我从不相信还有什么另一个世界。这就是我的悲剧所在。
父亲那个时候不仅艺高胆大,而且时常风光地抛头露面——当翻译。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城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和市民听不懂北方话。北方干部做报告需要方言翻译。父亲的第一个翻译对象是省委书记。渐渐地出了名,父亲成了北方干部与这个城市工人之间的语言桥梁。并肩与各种头面人物站在讲台上,模仿他们的手势和口吻滔滔不绝。那时的父亲声音嘹亮,神采奕奕,踌躇满志,如同一粒饱满的种子立即就要脱颖而出。父亲肯定没有料想到,这就是他最为辉煌的时刻。不久以后,上帝轻轻地弹了弹手指,这粒种子骨碌碌地滚到了一个水泥旮旯里面,再没有发芽的机会。剩下的日子里,这一段短暂的翻译生涯成了父亲的收藏之中最为贵重的记忆。
我相信曾经有过一个意气风发的父亲。我固执地寻找这种父亲的形象。我无法想象的是两种父亲形象之间的落差。哪一天开始,父亲变得目光黯淡,忧心忡忡了呢?现在,我终于明白,解释父亲形象的转折就是这本书的使命。
附录:父亲手记(二)
1953年,大张旗鼓的“三反、五反”运动进入了对不法资本家反“五毒”阶段。福州市在现在的“五一广场”召开五万人大会,全市通过有线广播家家收听大会实况。大会由市委书记主持。省委书记也到场,但不露面,而是隐在“健身房”内,省委宣传处长在场内骑着自行车往来于“健身房”与主席台,传达省委书记对于会议的指示。
广场南端新搭一座高大的主席台,分两层。下面一层留给被批斗的资本家坦白用的,只设了麦克风。第一层后面搭起的第二层才是真正的主席台。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全场,还可以看到第一层发生的一切。主席台设两部麦克风,一部由市委书记用,另一部由我用来翻译。今天的翻译有些特殊。
市委书记交代:我向全场翻译他的讲话,还要把坦白人当场用福州话坦白的内容翻译给他听。同时,翻译市委书记的讲话时,他厉声。我也要厉声,他大骂,我也要大骂!
作为全省全市资本家的典型, 当天上台坦白“五毒”罪行的大小资本家共六名。第一个重头戏是福州市爆竹行C老板。我不断地把C老板的坦白翻译给站在旁边的市委书记。突然,书
记一声凌厉的断喝,连珠炮似的责问、揭露打断了C老板的坦白。我立即就仿照书记的腔调厉声用福州话断喝、责问……坦白又继续了,我立即又变个角色成了坦白人的传声筒,突然一阵大骂,我又马上换个角色……全场只有我最忙,说的话最多。C老板下去了,换一个上来,每次都得才丁断好几次。其中居然上来一个我的初中同学X,广东人,这时已经当上老板了。他是用普通话坦白,我还得把它翻译成福州话当场向全下广播。六人中有的是坦白从宽的典型,有的是顽固不化、从严处理的典型,市委书记的口气、腔调、说法都不一样,我演戏似的鹦鹅学舌跟着转场。
通常说好翻译的标准是所谓“信达雅”。从我的特殊对象出发,我以为应把“雅”改为“俗”。我就是倚重这个“俗”字,博得广大工人和市民的欢迎。我的口译不完全只是把应译的话变个话音,还时常要找到相应于北方话的福州话语汇,许多都是“土白”。许多“土白’’是写不出的。它们往往只在没有什么文化的那一阶层人群中流通。一般的“学生哥”说不来,甚至难得听到。如果翻译得准确,给听者的印象特别深,而且会记得很牢,过后还津津乐道。我之所以熟悉这类地方群众语言,主要得益于小时喜欢听“福州评话”。评话的语汇极其丰富、通俗,许多只有音而写不出字,可是生动得很。解放后,我在工人中混的时间多了,出于做群众工作的需要,也用心学着说。我的这个特点,至今一些工人老朋友还印象深刻。
紧张的气氛终于酿成了一个事件。某一天半夜,报警的钟声响彻校园。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学生宿舍。所有的学生都被集中到食堂,特务按照黑名单捕人。抗议、逃跑和特务示威的枪声混成一片。这大约是父亲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场面。L君和父亲都未曾列入黑名单,但是,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憎恶有增无减。大夏大学的学潮肯定使国民党当局深为恼火。没过多少天,当局借口局势紧张而宣布大夏大学解散。
父亲短暂的大学生涯就此结束。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父亲就读的大夏大学旧址。一条小河横穿校园,波光粼粼,两岸柳树依依。暮色溶溶之际,这是我散步的必经之路。河上一个小亭,刚刚修缮不久。父亲说,当年他曾经拍摄了一幅这个亭子和水中的倒影,相片冲洗出来之后入选大夏大学的十幅校景之一。父亲于1949年离开大夏大学,我于1982年踏人华东师范大学。三十二年的沧桑,今夕何夕?父亲的皱纹写在脸上,感慨存在心上;我的皱纹写在心上,感慨落在纸上。
附录:分量
1977年的夏季,我是一个手执镰刀、衣裳褴褛的农民伫立在田头。我的手心结了很厚的老茧,内心日甚一日地迟钝。恢复大学考试的传闻断断续续地飘来,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大
学”这个字眼距离我的生活已经十分遥远,我从未觉得那一圈围墙里面还会和我有什么联系。我的理想是争取做一个不坏的木匠。
可是,消息日渐一日地明朗,周围都在蠢蠢欲动,考试终于成了一件事。当然,也就是一件可以试一试的事情而已,我不允许自己寄予过多的乐观想象。那时已经没有志气将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家作为后半生的偶像,学术如同天方夜谭,大学录取的真实意义是口粮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不敢轻易地相信命运的慷慨大方。我的父母亲曾经作为下放干部滞留乡村多年,我深知要将户口搬回城市会遇到多少额外的麻烦。这是中断了千年之后的大学考试,预测的录取率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这个数字倒是没有吓住我,这个数字比我可能返回城市当一个工人的概率高得多了。
温习功课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自恃比别人多读了一两首唐诗宋词,中学曾经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于是决定报考中国语言文学系。有趣的是,功课温习奇怪地召回了我的数学兴趣。我徜徉在一批数学练习题之间,乐不思蜀,以至于不想理会我从未读过的历史与地理。幸亏妹妹及时提醒了我。她报考的是理工大学,但她认为我的数学水平早就不亚于她了。日后得知,我的数学几乎得了满分;数学方面的超额收入恰好补偿了历史与地理的亏欠。这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奇怪的是,现今我再也记不起我是在哪一个考场进行大学考试——估计是我插队所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或者中学。记住的竟然是考试前后的一些零星片断:时常忧虑准考证丢失,惧怕政治审查受阻而面对表格愁眉苦脸,体检时就着水龙头喝一肚子凉水降低血压,因为嗅不出三个
小瓶子里汽油、酱油和水的差别而大惊失色,如此等等。在我的心目中,这一切要比那几张考卷凶险得多。
忙乱过去之后,我就不愿再想这件事了。天气逐渐凉了下来,一年将尽,似乎没有人知道这次考试的结局是什么。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在另一个知识青年家中闲扯。他忽然提到,为什么这么久了竟然没有大学发榜的消息——莫非又有了什么变卦?这话惹出的焦虑让我有些坐不住,我起身回家——到家的时候恰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薄薄的一张纸片:厦门大学中文系。悬在半空中的情绪突然松懈了,一时百感难言。这一刻开始,我才真实地掂量出这场考试的分量。
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意味了什么呢?他似乎正在思考生活下去是否值得。如果一个时代如此不堪,人们有权利选择不活。多数人掌握不了历史,那就退而求其次——那就掌握自己好了。自杀是选择一时的痛苦解脱长久的痛苦。自杀,把脸从一个如此不堪的时代那里转开,这就是对于世界的评价。所以,加缪认为,自杀与否是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式的自杀通常难免一死。这种自杀是深思熟虑、多方衡量之后的结论。从第一个闪念开始,哲学式的自杀就是进行式的。自杀的愿望如同癌细胞不屈不挠地繁殖,拦也拦不住。哲学式的自杀来得及精心设计各种独具一格的形式。上吊,卧轨,利刃剖腹,服用安眠药,把煤气管含在嘴里,选择一个风景如画的大桥跳下去,用一根筷子深深地捅进自己的鼻孔,将一管猎枪顶住下巴扣动扳机,如此等等。哲学式的自杀死得从容不迫。某些特工或者间谍被捕的时候咬破了藏在衣领上的毒药,这仍然可以归人哲学式自杀的范畴——不仅因为蓄谋已久的设计,同时还因为一个基本的判断:囚徒的生涯不值得眷恋;囚徒的痛苦和耻辱远远超过死亡。
相对地说,另一种自杀是爆发式的。短短的某一个时刻,精神或者肉体仿佛再也迈不过一个坎了。无法忍受的剧痛,一片混乱的思想,喘不过气来,一切都在崩溃,整个世界仿佛开始了古怪的抽搐。彻底的绝望夜幕一般地罩下来——死亡的念头突如其来地覆盖了全部领域。除了自杀,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几分钟之内,命悬一线的危机不可思议地降临。这就是爆发式的自杀。但是,如同父亲身上发生的那样,这种绝望来得快,往往去得也快。只要有一个小小的障碍——例如,父亲同事的目光——干扰了自杀的冲动,水银柱就会迅速地降下来。风波平息。精神渐渐稳定。爆发式自杀如同心脏病的突然发作。尽管险象丛生,然而,如果及时服用硝酸甘油片,挨过了这个关口又可以再活几十年。
爆发式的自杀念头通常是在一个异常的环境之中产生。这种环境如此无理、蛮横、粗暴、残忍,历史一下子变得如此可鄙,这一口气实在吞不下去。心理的狂躁突然势不可遏。自杀,
用死亡作为抗议——愤怒就是在这个时刻一下子漫过于理性的堤坝。爆发式的自杀不存在一个周密的设计。几乎可以说,父亲的自杀念头很大程度上是被那一扇窗户挑起来的。幸运的是,
邓一扇窗户对于父亲的危险诱惑仅仅存在了几分钟。
许多人听说过歌德的例子——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写作之中释放了失恋的沮丧,挣脱了自杀情结的追踪。歌德为汁么比自杀名单上的那些作家幸运,这是文学教授们的题目。尽管文学教科书还没有给出一个定论,但是,自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流行之后,文学有助于解除焦虑的观点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父亲打消了自杀情结与文学无关。然而,必须承认,随后而来的文学阅读对于他的精神平衡肯定大有裨益。
三百天的后期,看管渐渐有些松懈,不再有人跟着父亲进食堂或者上厕所;阅览室也开始允许父亲进入。父亲争取到了借书的权利,每次一本。父亲记忆之中,阅览室约有八九个书橱,藏书千余本,算个小图书馆,绝大部分是文科著作。父亲大约两天可以读一本。因为担心过于招摇,父亲不敢频繁地换书。一个傍晚,父亲顺路拐人阅览室时发现,管理员不在,书橱的钥匙扔在那里。父亲打开书橱取出一本小说,离开时干脆将钥匙带走。此后,父亲总是在人们吃晚饭的时候偷偷来到阅览室换书。白天他先到阅览室侦察哪一橱、哪一层的哪一本,晚饭时摸黑进来,打开书橱用手摸着数到第几本,新旧对调,不过一二分钟。延续了几个月,父亲基本读遍了这个阅览室里的藏书。令人惊异的是,这一场鬼鬼祟祟的阅读竟然始终没有被发现。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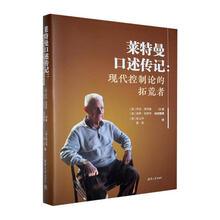



早就知道有这本书——本来要过些年才会动笔写的书。现在,它却急不可耐地冲出来,逼迫我修改写作计划。父亲不是一个爱表现的人,母亲甚至畏惧公众。所以,这种情况只能解释为某种历史的急迫性。我只得提早开始了。
我面对的是长辈的历史,似乎是遥远的过去。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他们身上有一些我们必须分担的历史之谜。否则,我又有什么必要把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塞给读者?他们太普通了,他们的经历丝毫算不上惊心动魄。父亲和母亲肯定是属于默默地生、默默地死的那一批草民。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时代”这个大词。
每一个人都可能看到自己的世界。每一个时刻都可能重新发现世界。这是部分章节背后存有附录的原因。附录的内容大致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谈论,可以与正文相互参证。几篇附录摘自父亲的手记,另外几篇附录是我以往写下的文字。
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不长,但是,我消耗了许许多多记忆和思想被重新犁过一遍,掩埋已久的岁月再度翻开了。笑声的确不多,叹息和沉重的感慨洒满了纸面
这辈子肯定会有这么一本书,也只会有一本。愿意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一定明白,为什么我这样说。
且将这本书献给我年迈的父亲和已经在九泉之下的母亲。
2003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