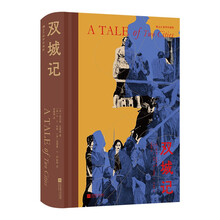我们当初有一种后来证明为错误的偏见,以为美国东西比中国贵得多,所以一切服装用品应当尽量在出国以前购备。多数同学在服装上花的钱太多了,但害处不仅是花钱太多,还带了些不必需与不适用的东西。<br> 据我个人的经验,在中国裁缝处定做的西装总不如在美国买的现成衣服配身舒适,皮鞋亦然。这是不应当多带衣着的一大理由,到士大的几个人还发现了些别的理由:那边的天气太好。衣服可以不分冬夏。那边的校风特别,平日可以穿绒线衫,黄绒袴,领带也不妨省略。所以只要一身蓝哗叽已够应付一切交际上的事变,其余都是不必需的。<br> 我们还有一种通病,是所带手提箱大大。“大”当然是好处,但“大”了不得不“重”,自己手提不便.若请教“跑腿”(Porter同音),每次美金一四开(或作一“瓜豆”,意即一元的四分之一),太不经济。<br> 最后,我愿意向准备出国的人进一忠告,劝他们在下列三种方案中选定一种:<br> (一)不要带茶叶。<br> (二)衣箱里不要放樟脑丸。<br> (三)茶叶要放在衣箱外面。<br> 任何第四种办法必至引起以下三种严重后果之一:<br> (一)将旅行过这样远路的茶叶全部放弃,怎舍得?<br> (二)将樟脑味已吸收至饱和点的茶叶自己享用,怎容忍?<br> (三)将世界闻名的中国茶叶请外国朋友欣赏,怎为国货宣传?<br> 在士大做学生的时候,曾经参观过两处留有深刻印象的地方,一处是阿奴疯人院,一处是李克观象台,非记一下不可。<br> 阿奴疯人院是加州州立的医院,专收精神病者。在美国,这类地方恐怕很少标明是疯人院的。普通只称为“医院”或“病院”,以免病人有不好的反感。阿奴离士大约一点钟的汽车路程,我们是一班选修变态心理学的学生,由教授带领前往,一共去了三次。同学中有好几个有车的,差不多足供全班同学乘坐。但第一次恰巧差一个坐位,一个比较轻的(身体地!)女同学说,“不要紧,我可以坐在石教授身上”,她就坐在石教授身上。后来两次石教授的夫人同去,不知怎的反而坐得下了,大概多了一个有车伪同学参加。<br> 病院规模很不小,非常整洁。宿舍分几处,按病人情形分派。每处尽量家庭化,除寝室外,有食堂、浴室、厕所、公共休息室,病人每天生活极有规则,除病重者,起息饮食都照规定时间,每星期有电影、跳舞、音乐会,各一次。大部分病人每天有指定工作,非但于经济上不无小补,于治疗上更有极大价值。病人每月纳费二十元至四十元,贫者可免。<br> 我们参观的主要目的是实地考察各种病象。每次由院中医生先讲病者历史与现状,再当众与病者谈话,以见其行动、态度、言语、思想的一班。所见病人可归入四类:<br> 一种病人完全生活于有系统的狂妄幻想中。幻想可以分为富贵荣华胜利一类(delusions of grandeur)与罪恶羞辱遭难一类(delusions of Persecution)。一个病人可以用这两种幻想,互相弥补,自圆其说,亲友的劝告辩论当然不能动摇其偏见,实际的环境事实也绝不能改变其自信的毫末。有—位病人自以为是拿破仑的后代,又说某铁路公司完全是他的私产,讲起来神气十足,同时深信有人设计陷害他,所以被禁于院中。另一个态度懊丧,言语又轻又慢的病者,自以为是罪大恶极的囚犯,他(想像中)的主要罪状是污辱自己的兄弟,逼迫他不得不自杀。此人曾在某公司当职员,因为他的兄弟资格虽然比他浅,位置却在其上,就很不快乐。后来脱离公司,独自营业,又不幸大亏其本,于是渐渐现出病态云。<br> 有一种称为“狂郁疯’(manic-depressive insanity),往往好了再发。发的时候,分“狂”与“郁”两种,也有两种轮流发的,中间隔着一段长短不一的常态时期。“狂”的病象是高兴而多动,态度乐观,终日仿佛忙得不了,言语既多且快,但毫无伦次,也不能安定于任何工作。一个病人刚走出病房,老远就向医生高呼早安,望到中国人的我,就说“我最喜欢支那市”,接着又指了每个参观者,说这个是谁,这个见过,这个不认识。与医生谈话,应对如流,但所答多不中肯。不一会就站起来要走,说她有很多事要做,临走扬着手帕向大家高呼“我爱,再见”。与她绝对相反的一个“郁”病者,走得非常之慢,坐下后丝毫不动,非问不答,答也只一二字,露出毫无生趣的样子。这种病人往往终日守着不变的姿势,坐了永远不想躺下,躺了永远不想走来。<br> 再一类是梅毒侵入中央神经系的结果。初患者病象并不显著,只是不负责任,轻浮夸张,奢侈浪费。渐渐就不能维持日常的工作,大言不惭会达到任伺人不会相信的程度。说起小老婆来,不肯以十个八个为度,一定要说有几千几万。说起任何游戏来,也不仅是略窥门径,一定要说所有国手都甘拜下风。病重时全身瘫痪,只存植物式的生命。<br> 最后一类是所谓“早衰”(dementia praecox),因为患者常是青年。主要的病象是与现实隔离,置环境于不问不闻,所以也称“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非但“泰山崩于前而色<br> 变”,任何好消息不能使病者面有笑容,任何恶消息也不能使他表露悲伤。专门术语所谓“否主义”(negativism),是一种不合作主义,一切命令,托嘱,或恳求,一概不理,甚至拒绝饮食,大小便也忍住不放。这类病者的大多数在大半时间不言不语,很像“郁”者,但有时会非常凶暴,打人毁物。也有像第一种那样固执着有系统的幻想的。还有一部分这类病人常表演机械式的姿势与动作,万分可笑;例如那天有一位,一手举着帽子不动,两腿轮流举起,并不前进,仿佛做体操时的“踏脚”。<br> 瀑布在冬日别有景致,瀑下冰片积凝,接两岸成桥,游客亦以走冰桥为常。某次,多人在冰桥之上,忽觉立脚处动摇,同时闻冰碎之声,知冰桥且离岸破裂,互促奔返两岸。有坎人施丹顿夫妇,在桥中部,闻声趋岸,以距远步艰呼援。有一美青年名希可克(Burrll Heacock)者,本已抵岸,至时奔返往救。至则冰已脱离两岸,随流而下,渐近漩涡急流。岸上人呼救火车至,亦无计可施,惟有从钢桥投绳索以候,希所立冰块先抵桥下,见索猛握,竟得悬身空中,见者无不欢呼。但桥高百六十呎,希于半途力尽下坠,卒溺冰下。施氏夫妇知已绝望,下跪互抱,于祈祷中遇难。<br> 士大中国学生从前很少,一大部分还是生长于美国的,所以会所虽小,还住不满,曾有高丽学生与美国学生寄寓过。我们到的那年刚住满,后来人数更多,会所不能容,常有住在会外<br> 者。我于第二年也搬到学校宿舍友宁堂去住了。<br> 据我所知,美国全国各大学只有三宅中国学生会会所。士大而外,就是加州大学与康奈耳大学。康大的那所有希腊字母的名称,与美国学生的兄弟会同样性质,并非全校的中国学生都是当然会员。加大的中国学生多,住在会所的就相对地少,房子也不在校址以内,并且并无膳食合作社那类组织,所以也不如士大的会所热闹。市大的会所非但解决了大多数中国学生的膳宿问题,也是全体中国学生的俱乐部。大家在课余都去坐坐,谈谈,看看报纸,听听无线电,开开留声机,如有送往迎来等事,便可在此开会,且不说联络感情的便利,万一同胞间意见不合,偶有争吵打架之必要,在此关着门举行,也可以免家丑外扬。<br> 但士大会所非但并未遗羞祖国,却还争到些光荣。照注册课将全校学生成绩按住所平均的结果,中国学生会至少有一度曾占首位。美国学生平常只晓得中国学生不大开口,在学生办的日刊上见了这段新闻,自然不胜惊愕。但平心而论,这实在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因为美国的大学教育太普及了,本国人进大学是比较容易的事,而且美国学生往往忙着课外活动,行有余力时才注意到功课。曾见某位幽默家(大概是Sto-phen Lacock)一篇形容美国大学生的文字:两个学生正在商议当天晚间应当怎样消遣,两人轮流着提出跳舞,戏剧,电影,音乐会,茶话会,辩论会,篮球比赛,打拳,角力,等等,但都被对方以“已经厌于此道”的理由反对,最后一个建议说;“有了!我的箱子底里有几本书,从未看过,不知究竟讲些什么,今晚让我翻出来,大家读一下罢!”<br> 友宁堂宿舍都是两人一间,各人一床一椅,另外合用一桌,一书架。一壁橱,一五斗橱,一面盆。后来在哥仑比亚大学的李文诗登堂住过一间,设备大致相同,但单人独住。在哈佛大学曾见某宿舍不备家具,须自己购买,或由前住者顶让。多数宿舍,如这几处,都是单租房间,不包膳食的。有人说宿舍中美国学生很会吵闹,有人说住宿舍可以多结交几个美国朋友,这些都不是完全对,也不是完全不对的意见。<br> 纽约河边路五百号万国公寓也是学校宿舍的格式,但不属于任何学校,是洛基非娄捐款建筑,专租给外国学生住的。房间虽小,床桌椅橱一切齐备,唯一美中不足之点是房里缺只面<br> 盆,只有每一层的公共洗面室,据说是为便利寄宿者联络感情起见。据我个人经验,很少人在刷牙洗面时有谈话的兴趣,尤其是早上,大家正赶紧洗完了好让候补者,谁有闲工夫谈话?但有效的联络感情方法还多呢:楼下的客厅,食堂,吸烟室,都是谈话的好地方,并且不时举行聚餐会跳舞会之类,只怕交际的工夫(并指时间与造就)不够,不怕交际的机会没有。有人因此说万国公寓不是读书地方,未免言之过甚,因为这些聚会是绝对不强迫的。<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