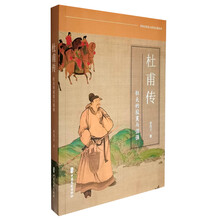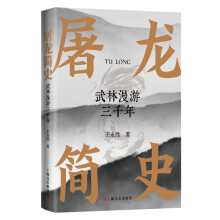她分明看见门的旁边黑兀兀地站着一个高大的人,她略停脚步,接着把宝剑一举,“飕”的一声追了过去,并厉声问说:“你是谁?”可是那条黑影已经很疾快地走进了靠右手的一条小过道,她剑光闪闪,身子随着剑光也紧追到那里,一看,什么也没有,她腾身上房,四下去望,也只能看见几处院中屋内的几片灯光,何妈妈跟另一个仆妇提着水壶正回到自己屋里去,<br> 此外就再无别物,她可真惊讶了,心说:“莫非真是那个腾云虎来了吗?”她赶紧跳下房去,急急走往前院,本想要大声嚷嚷一下,却又赶紧将自己拦住,望见了仆人住的那屋中灯光灼灼,话语嚣杂,大概连苏禄,带打更的耿四全都在这里谈天了。她来到门前先轻轻将宝剑放在墙旁立着,然后,蓦地一开门,向屋里说:“净说闲话了!”屋里的杂乱之声,当时就都停止了,十几对惊讶的眼睛看见了立在门外的小姐,就都慌了,有的赶紧拿光着的脚丫向炕下去找鞋,耿四先问说:“小姐,有什么事吗?”小琴却淡淡地说:“没有什么事,只是,今晚你们全不许睡觉!勤打更,有刀的预备在身畔,听见了没有?”屋里的人一听了这话,吓得脸全白了,有的点头,有的发着怔答应,耿四却说:“小姐您就收心吧!有我值夜,他贼!贼的屁也来不了!”小琴把门关上,拿起剑来,两眼又不住地东瞧西望,又飞身上了房,就如狸猫似的,踏着屋瓦,很快地就来到了那东跨院,轻轻地落地,脚下无声,一看,东屋的大嫂以后睡了,屋中一点灯亮也没有,西屋里三哥的那对铁球还不住“叮哨叮哨”乱响。她将剑藏于身后,蹑着脚步往那窗前走去,就听苏振杰正跟他妻子说:“你知道吗?咱妹妹这回的武艺出了名,以后的麻烦少不了,不定有多少江湖的少年侠士来求亲呢!我倒愁得慌,她也不是小孩啦,我瞧她早就想着找女婿……”小琴在外一听了这话,反倒脚步更轻,脸发烧,心里气,可是不能说话。<br> 她又“飕”地一声上了房,同时故意抡起宝剑向屋瓦上蓦然—剁,“吭”的一声,下面屋里的苏振杰“啊呀”了一声,连问:“谁呀?谁呀?”又大喊着:“来人哟……”三嫂也尖声地嚷叫。小琴却已越过屋脊,又飘然跳下了正院之中,开门进了北屋,却又不禁一阵惊愕,只见李大姐,何妈妈,还有一个吴妈都在屋里,那高身材,穿着旧夹袄,花白胡子的李伯父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屋里了。小琴搁下了宝剑,自己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先笑着叫声:“李伯父!”然后又过去拉了拉李大姐的手,又笑着说:“我已嘱咐他们,不让他们睡觉了,今夜里大概不至于有什么事,——即或有事,你也不必惊恐,有我,有我三哥,还有李老伯呢?无论他什么样的强盗来了,咱们也不怕!”李老英雄在那里盯着她们,沉着一张不高兴的脸。这时院里就乱了起来,脚步声,说话声,苏振杰拿着宝剑惊慌慌地进来,说:“妹妹!你刚才没听见吗?房上有人!一定是那腾云虎来了!”说着话还不住喘息。外面搬梯子声,纷纷谈话声,大声骂贼声,更是乱,灯光照得窗子也闪烁惊人,吓得何妈妈跟吴妈都面如土色,身子直抖。小琴却一点也不惊慌,笑了笑说:“什么事情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呢?吓坏了人不要紧,叫李伯父看着有多笑话呢?”这时李老英雄只站在那里不说话,李大姐却不住翻眼偷瞧她的父亲,态度好像带着点羞悔。小琴就向她三哥说:“你出屋,告诉他们,搜查可以,巡守也可以,别瞎喊叫!别人还得睡觉呢!这是怎么回事呀!”又向李老英雄笑笑说:“伯父您请坐吧!您别不放心!”李老英雄只点了点头,却又瞪了他的女儿一眼,说:“你回西屋里去吧。”李大姐深深地低着头,又一步迈不了三寸地慢慢走出屋去了,小琴笑着往外送,并叫吴妈赶上去搀扶。此时院中那些仆人虽未散去,可是纷乱之声已经停止。<br> 他把老太爷夸赞他的话,跟楚江涯佩服他的话都说了,李大姐是只在那里深深地低着头,而小琴几乎要笑出来,可是心中太悲痛了,她笑不出。待到苏振杰又说出了云媚儿之名,小琴却忿然地说:“你告诉爸爸,叫他老人家不要怕就是了。什么云媚儿,要是来了,由我一个人抵挡!”苏振杰却皱眉说:“爸爸偏不要你,说你是个姑娘,不愿叫你出头露面。”小琴说:“来的又是一个女贼,我跟她斗一斗,又算什么!”苏振杰说:“我也觉得不算什么,你跟那些个大汉子都已打过了,来个女贼,就是你把她拖住,抱住,两个人滚在一块儿,也不要紧呀!可是爸爸不容我劝,他说是不能叫人把你看成江湖女子,将来你还得嫁官宦之家,去作一品夫人呢!”小琴听了,脸上一阵红,同时簌簌地落下了眼泪。苏振杰还以为她是被这话气的呢,但没有料到她真伤了心,竟呜咽地哭了起来,他不禁发呆了。他转脸看看李大姐的头也低得更向下,娇脸儿上也笼罩着一层忧郁,这层忧郁可更显得妩媚堪怜。苏振杰就直着眼睛看了半天,随后就问:“到底你帮助我不帮助我呀?我可是不怕云媚儿,不过一个江湖女子,一定是泼泼辣辣的,叫我怎么跟她缠呢?”小琴却拭着泪叹气说:“到时候再说吧!反正若有人要来伤害爸爸,我绝不能够看着不管。我也很愿意来的是个凶贼,我杀死她,同时她也杀死我!”苏振杰说:“哪能够呢?云媚儿连楚江涯那小子都抵不过,自然也抵不过我,更抵不过你。只是……”又笑眯嘻地说:“李大妹妹,到了时候别受了惊就是了!”此时忽听窗外一声咳嗽,他了一大跳,小琴颜色也变了,赶紧擦干了脸上的泪迹。这时候苏老太爷又咳嗽了一声,就拉开门,走进屋来,苏振杰嚅嚅地叫了一声:“爸爸。”赶紧就走了出去,小琴却脸通红,笑着说:“爸爸你别瞒我,我都知道了,可是您放心,既然有我哥哥啦,到时我就得不管且不管。可是我得保护着您,不能叫贼人伤了您的一根胡子!”老太爷却沉着脸,只是盯着李大姐,忽然问说:“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刚才的事你也听见了?有人要来杀我,你在这里,万一受了误伤,我对不起你的父亲,我想,明后天就派个妥当的人,把你送往婆家去!”<br> 小琴听了这话,神情就变为奇惨,她急急地说:“这怎么可以呢?人家,我大姐的腿又有病!”苏老大爷鼓励地说:“腿有病也得走!不是我不顾念旧友之女,是咱们家里眼看就要出事……”小琴忿然说:“有我保护着她!”老太爷用目瞪着女儿说:“连我都不用你保护,你得知道,你是个姑娘家,你年已不小了,我家是书香之家,你二哥是父母官,县太爷,你就是个千金小姐。”小琴说:“我不愿意当什么千金小姐!”老太爷怒斥说:“不识抬举!我不在家里,你抛头露面,卖弄武艺,伤了鲁家五虎,又与楚江涯那些个江湖人,深夜在野外拼斗,也够丢尽了我家的颜面!我不说你,你还不知足?还要……”小琴哭着,拉着父亲的胳臂说:“爸爸!……你说我打我都行,只是李大姐……人家,人家不愿到婆家去!”苏老太爷说:“什么话?女孩子家要明白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订了婆家,为什么不去?这都是江湖人没家教。”小琴说:“爸爸有家教?爸爸你就不是江湖人?当年若不是李伯父救了您的命?……无论如何我不能……”她呜呜地哭,并且跺脚说:“我离小开我李大姐!我不能就看着您把人家赶出去。”老太爷大怒,骂着:“混蛋!不要脸的丫头!你敢拦住我?我白疼了你!去”他用力把女儿一抡,可是小琴揪住了他,不能抡开,他扬起手来又要打。这时李大姐突然跳下炕来,一手将他的胳膊托住了,使他的胳膊落不下来。他忿怒,吼叫了起来,说:“你也敢……”但,他忽然觉得右胳膊一阵麻木,他大吃了一惊,紫脸立时变成了苍白,胡子都直颤动,赶紧夺开了胳膊向后退了两步,“光当”一声,撞翻了一把椅子,震倒了桌上的花瓶。他丢了魂一般地惊讶,瞪大了双目盯着李大姐的两只脚,李大姐是浅红色的拖地长裤,露着尖尖的鞋头儿。老太爷简直说不出一句话来了,口中只叫着:“啊!啊!”只是点头,小琴却一步上前就跪下了,并抱住了她父亲的双腿。<br> 我现在就要说铁臂刘得飞,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那年,他就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胳臂据说有人用一辆满载着大石头的牛车的轮子去轧,也损伤不了一点,我没看见,我也不大相信,但他确实有真功夫,直到七八十岁时,双手要举沉重的石锁和“仙人担”,还是一点也不吃力。这只是说他的浑厚的力气,和健强的身体,尚武的精神;至于他一生的侠义行为,悲壮事迹,更多是令人可泣可歌。 刘得飞生在“京西”的门头沟,那地方是一片煤田,在滑末时,就早已有人用旧式的方法开采,卖给城里,那运输的器具——就是骆驼。<br> 骆驼是一种庞然大物,然而它的头不大,尾巴尤小,四条细腿支着一个巨船似的身子,按说应当不大稳吧?但它的蹄子,即脚却是很大,走起路来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好像是个老于世故、艰苦而负重的人。它的身子又真富于曲线美,在背上是两个高高的“驼峰”,是天然的一副鞍鞘,像生下就为人骑或址放东西用的。<br> 这家伙大概生在寒带,所以不怕冷而怕热,它的胃部构造很是特别,一次喝足了水,就可以存蓄起来,三天五天也不会渴,它最能显露本领的地方是蒙古一带的沙漠,所谓“沙漠中的旱船”就是它。它的巨大的蹄子踏着万里的荒沙,据说真比马还快,它能够水草一点也不进,安然地渡过了旱海,走到甘泉,蒙古人跟它是好朋友,北平因为地理上的关系,距离蒙古很近,所以就把它请了来,豢养着它,不叫它作别的,只叫它驮煤。<br> 养骆驼的人家多半在门头沟,夏天还得带着它到海边,最好是秦皇岛——去避暑。北平的秋风一起,落叶翻飞,它就得回来了,因为这时家家户户,都得买些煤,都得叫它驮运,天气愈冷,它的工作愈为繁忙,在北平随时可以看到,一串一串的,每一串至少有七八匹都用绳儿穿着鼻子,颈上还挂着铃铛,随走随发出“叮啷哨啷”的悠扬而美妙的声音,如同安慰着人们的寂寞。拉骆驼的人年纪不能太老,还须要有两膀子的力气,因为每当将大袋的煤运到人的家门口时,骆驼就把前后腿都一屈,向地下跪倒,这就算是休息了,它可不能进人的家门口,因为它的身体太大,这就必须拉骆驼的人将驼峰之间放着的大袋的煤,每袋至少也有一百来斤,背在肩头上运进了人的家,倾在院中,或是倒在仓库里。<br> 刘得飞就是这么一个拉骆驼的小伙子。那时他年才十五岁,什么事也不懂,他没有父母,每天只是跟着叔父刘大脖子拉骆驼运煤。起先他只能作“拉”跟“看”的工作,现在,他算是长成人了,他就也帮助扛,沉重的煤袋压在他小小的肩头,他并不觉着吃重,而且他逐渐往上去添,后来他竟能背负二百多斤的重量,同行的人没有一个比得过他。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