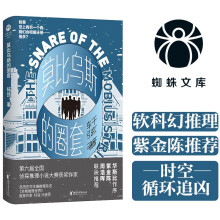林白最近引人关注的作品是《妇女闲聊录》。一般读者的反应我不得而
知,批评家们则(几乎)一致叫好,评价很高。但我的感觉完全不同。也许是
我对这部作品的好处至今仍比较隔膜,所以反应迟钝。虽然我以极大的耐心
读完了这部作品,但它丝毫没有激发起我的兴奋感,也谈不上任何阅读快感
,甚至还几次想弃之不看了。这部作品难道没有新鲜感吗?决非如此。它的
语言、文体和故事,对我都是非常新鲜的。而且,从我所了解的林白其人其
作的历史来看,她写这部作品的理由和状态,对我也是新鲜的。那我为什么
非但没有阅读好感并还会产生厌倦心理呢?(我的这种感觉如果稍嫌表达过分
的话,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我对这部作品是不以为然的。)下面可以简单地说
明一下我的理由,就算是读后感吧。
首先是这部作品的语言(叙述)方式。它是用近乎完全的口语、口述的“
实录”方式构成的,其中还夹杂了大量的方言。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
长篇小说,这种方式显然是非常极端的。对此,有人或许会誉之为文学(语
言)的“革命”创举。但从我的文学观念和经验判断(特别是实际阅读的体验
)来看,口语、口述的实录必然会带来表达(叙述)上的支离破碎和重复累赘
,而这种后果对文学作品非但毫无文学意义,而且还是深刻的伤害。方言的
频繁乃至过度使用,后果也同样如此。我认为《闲聊录》在语言(叙述)上的
这种极端方式,实际上会造成并不断增加阅读的疲劳感和倦怠感,说得严重
一点,这种方式其实是在拒绝读者的阅读。
但是显然,作者对此倒是刻意为之的,许多批评家也持赞赏态度。这就
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语言(叙述)方式究竟有无文学的(革命)价值?抽象地(
从理论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我想不会有太大意义;专就《闲聊录》来说
,我的回答无疑更多是倾向于否定的。语言(叙述)方式上的极端性,或许对
作者的写作动机(心态)具有某种快感,也或许会迎合或暗合了某种社会观念
和文化理论,但就文学语言的成熟度而言,极端性的主要价值无非体现在实
验性方面。如果说《闲聊录》在语言(叙述)上多少真有点文学的(革命)价值
,那我也只能在实验性意义上对其有所(保留性地)肯定。而它在这方面的过
度和极端,则足以令我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种实验其实是此路不通。通
俗地说,这不是小说,或,小说不能这样写法。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弗吉尼
亚·伍尔芙说过的一段话的大意。她说,自己这一代作家的作品,包括乔伊
斯等人,充其量只是文学的手稿;真正的大师,还是托尔斯泰。我想说的是
,实验或文学革命乃至颠覆,当然也是需要的,并有所文学价值,甚至还会
形成一种时势,但它也就仅此而已了,并不能构成成熟的文学(作品)形态。
实验与成熟之间,距离应该是明显存在的。我以为伍尔芙有超越同侪的明智
和文学判断力,而且,眼界阔大。许多批评家对《闲聊录》的褒扬,我其实
能够理解其中的缘由,但说一句得罪同行的不恭敬的话,我认为其中有失对
文学(作品)的一些基本判断。是不是一眼看到了这样一部“惊世”之作太激
动了所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