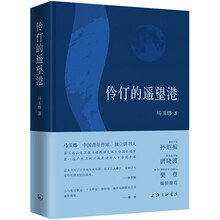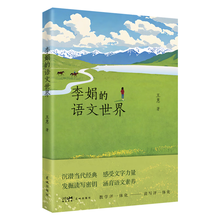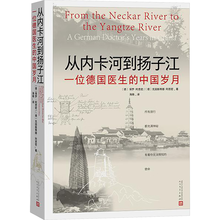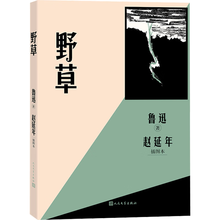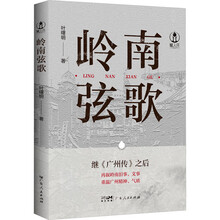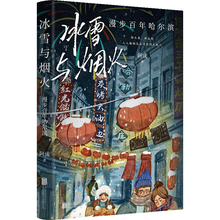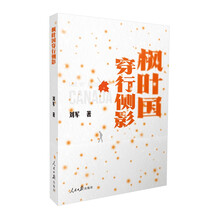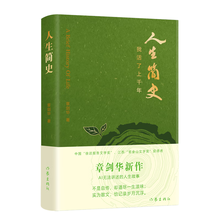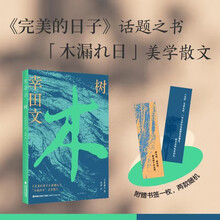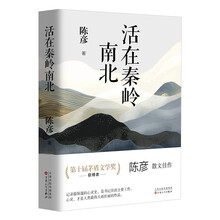尽管在小说中巴金如此强烈地表达了他的批判精神和乌托邦式的幻想,但是他还是流露出茫然的心绪和悲哀的情调,这种情调一直充塞着他的全部作品。巴金曾写道:“我的生活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巴金的这种彼此对立的情绪,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极大的困惑,这使他的价值判断时常陷入到窘境里。他无法解脱来自心灵的各种冲突,这样,他的理性认识的二律背反现象就显而易见了。
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反思上。《激流三部曲》、《寒夜》等小说全面地表现了他对家庭问题的认识,旧式的家庭在巴金眼里是一座“坟墓”,《激流三部曲》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庭的虚伪性和陈腐性。巴金认为,旧的家族结构已不再适应人的先天的本性和快乐原则,它完全颠倒了人的生命发展规律。这种家庭结构与人的自由意识是对立的,它以静态的超稳定性,窒息着人的生命的自由发展。它不仅亵渎了人的自由的本性,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桎梏。在高老太爷、冯乐山、克安、克定等人身上,巴金看到了这一旧的家庭结构的罪恶。
但是,巴金对旧的家庭结构的认识还停留在人道主义的层次上。当他看到旧的家庭结构的崩溃给人们带来悲剧命运时,他的批判锋芒就减弱了。他对以往的统治者以及旧家庭中的没落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憩园》可以说是巴金的这一矛盾的思想的最充分的体现。作者对杨三老汉的哀叹,对父与子间友情的认可,已完全脱落了《激流三部曲》那种冷峻的批判意识。在《激流三部曲》中,家长是罪恶的化身,父与子是对峙的两种势力,而在《憩园》里,这种情感被否定了,它被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所代替。巴金不时地对破落地主杨三老汉倾注着痛惜之情,他甚至希望人们应该用爱去给这位没落者带来慰藉。这时他似乎希望人们再返回到一种稳定的家庭结构里,因为在他看来,旧有的家庭结构的解体同时也使人失去了情感的纽带,人的精神开始跌入无底的深谷。巴金隐约地向人们表明,家庭是人的现实精神与情感的归宿,它的崩溃意味着人的精神和谐的丧失。因此人们不能超越这一社会形态而生存,否则它会使人处于无根的精神的漂泊中。
在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中,巴金同样地陷入了困境里。他一方面反对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在宗教启悟下的道德完善,另一方面又对孱弱的自我完善受难者的人格加以礼赞。当他高举着反封建的旗帜张扬自由精神时,他对杜大心、陈真、吴仁民、高觉慧等形象是充满爱戴之情的,而对周如水、高觉新、汪文宣等形象则持有批判态度;当他把善良意识做为人的优良品格加以宠爱时,他却对高觉新、汪文宣等形象的人格加以认可,巴金似乎觉得,在这些人物身上,蕴藏着人类尚未泯灭的人性的光辉。这时他对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的善良品德给予同情。沿着这一条路线出发,巴金把理想的人格逐渐由叛逆者的形象转向温柔慈善的仁爱者的形象。《第四病室》中的杨大夫是巴金这一思想的完成者,她的仁慈的精神,她的充满怜悯与爱的情感,在巴金看来都是理想人格的真实体现,在这里,巴金又回到了托尔斯泰主义的道路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