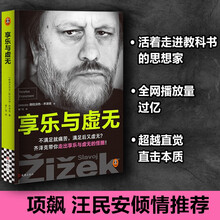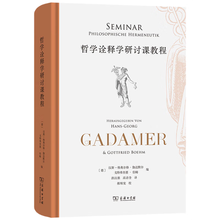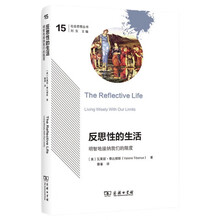对这个体系的质疑也用不着等待一种德里达式的或是罗兰·巴特式的解构主义的严密论证。正如里奥·布罗迪在其《历史与小说的叙事形式:休姆、菲尔丁与吉邦》与海顿·怀特在其《元历史》①中所展示的,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学家来说,写作历史已经成为了疑难事业,对自维柯以来的现代历史学家来说更是如此。无疑,这对修昔底德与普鲁塔克,甚至对希罗多德来说都是颇有疑问的。恰如詹姆斯显现最后的隐喻所暗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意识地戴上了“历史的面具”,很像演员穿上戏装、粉饰化妆一般。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相信奥兰治的威廉是个神话,或者相信阿拉瓦公爵是虚构的,而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叙述历史的先后顺序,实际上涉及了一个建构性的、阐释性的和虚构的行为。历史学家早已知道,在历史和叙述历史之间,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吻合。所以,我在这里简要描述的有关历史设定的体系,不仅对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就是对(把自己的事业模拟为叙事的历史学家的)小说家来说,都有一种巨大的、带有强制性的蛊惑力。这个体系不可思议地趋向于把自己编织成一种新的形式,哪怕它已经被人为地取消了也是如此,就像一个蜘蛛网又织出了我们西方语言的内部范畴,或者像佩内洛普的网一样,晚上被破坏之后,早上又重新编织而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