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从圣地回来时,在离索克斯和夏特努不远的奥尔内村附近,买了果农的一栋房子,房子藏匿在树木繁茂的山林里。房屋四周高低不平的沙质地是一片荒弃的果园,果园尽头是一条小溪和一排矮栗树。我觉得这狭小的空间适于寄托我长久以来的梦想:spatio brevi spem:longam reseces。我在那里种下的树正在成长。它们现在还很矮小,我站在它们和太阳之间,可以荫蔽它们。一天,它们将偿还我的荫蔽,像我呵护它们的青春一样,护佑我的迟暮之年。这些树是我尽可能从我浪游过的各个地方挑选而来的:它们让我想起我的历次旅行。而且在我心灵深处孕育其他幻想。
如果有一天波旁家族重新登上宝座,作为对我的忠诚的报偿,我只要求他们让我变得富有,使我有能力买下这座房屋周边一带的树木,使其成为我的遗产的一部分。于是我萌生了野心,想将我的散步场所扩大几亩地:虽然我是一个到处奔走的骑士,但我有修道士的深居简出的爱好。从我搬进这座僻静的居所以来,我出门不过三次。待我的松树、我的杉树、我的落叶松、我的柏树长大,狼谷就会变成一座真正的查尔特勒修道院。当伏尔泰1694年2月20日在夏特内出生的时候,《基督教真谛》的作者1807年选作隐居地的山丘是个什么模样呢?我喜欢这块地方。对于我,它取代我父亲的田野。我用我的幻想和熬夜的产品支付它,依靠阿达拉的辽阔的蛮荒之地,我才有这小小的奥尔内蛮荒之地;而且为了给自己营造这片隐居地,我没有像美洲殖民者那样掠夺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我对我的树木一往情深;我向它们奉献哀歌、十四行诗、颂歌。它们当中的每一棵都接受过我亲手的照料,我在它们根部都除过虫,我在它们叶子上都捉过毛虫。我对待每棵树都像对待我的孩子,给每棵都取了名字:这就是我的家,我惟一的家,我希望死在我的亲人身边。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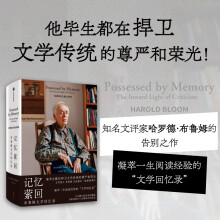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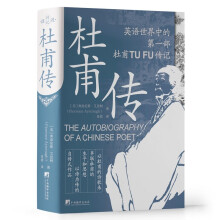
这部出版于一八四八年的作品,不只是作者私人生活的一本账簿,而是文学纪念碑式的一部巨著与史诗。它记录了作者的生命与思想,也记载着他的国家,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
加埃唐·皮孔的《世纪文学史》把这本书称为西方现代小说的榜样。皮埃尔·布吕奈尔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把这本书视为第一个现代小说家撰写的得到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的完全不像古典小说的作品,认为它标志着一种新人和现代文学的产生……
这部书是夏多布里昂众多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它使作者的不朽名字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获得永久的地位与名声。大作家雨果在小学作业本里这样写: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