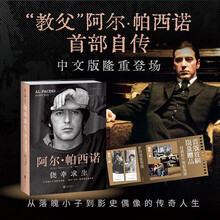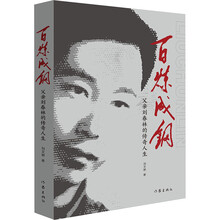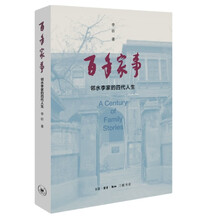书摘<br> 近代福建人文荟萃的一个直接因素是近代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当地的土绅对家族成员教育之重视及其结果上文已经有所述及。除此之外,在福建为官的士绅也为福建自从朱熹大兴教育事业所形成的尊师重教重道风气所熏染,因而对福建的文化教育事业极为重视。根据方彦寿的《朱熹书院门人考》所记载与朱熹有关的书院达到67所。其中朱熹创办的有4所在福建。朱熹讲过学的书院共有47所,其中在福建的有16所。还有朱熹题过词或者题过诗、题过匾额的书院共13所,在福建的有5所。在朱熹所创办的4所书院中,朱熹的及门弟子共有276人。根据何绵山的统计,可以考证清楚的朱熹及门弟子共有511人。在宋元时期的福建,朱熹及其弟子的活动足迹到处可见。诸如书院、碑刻、题词题诗题匾额、徒子徒孙事迹传说,更是遍及于福建的城市乡村。所以福建人以读书为荣、以办教育为神圣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根据郑孝胥早年的日记,仅仅福州市区的书院就有鳌峰书院、越山书院、蒙泉山馆、致用书随、风池书院、苍霞精舍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鳌峰书院。<br> 下面是应沈瑜庆之请写于1892年4月20日的《夜识亭记》:<br> 沈文肃公晚在金陵,常有退志,从容语僚属曰:士君子之操行,惟以不贪为主,则所持者简而易全,所取者淡而易置。以吾所见,当世功名之士,类皆嗜多务进,莫知所止,其于事为行止之间,坐是溃决而不竟,其出而不收者,众矣。某之去江西,行李囊橐一如始来时,非矫以取名也,亦卿以检制吾心使不得放云尔。见今世卿大夫家居,率得有园林亭榭之乐,使某遂得请归,亦欲买小园,茸木为亭,植忍冬覆之,而取杜诗“不贪夜识金银气”之语,题之曰“夜识”,庶以粗完平生之意。然未几薨于任,奉旨建祠于福州会城,因就乌石山许氏之涛园以为公祠。光绪十八年,叔子爱苍于金陵以语孝胥,且曰:“涛园有隙地,将如先子言,茸亭其中,吾子其以为之记。”闽中伟人,道、咸以来海内所推服者,林文忠公及公而已。文忠恢杰综博,而公简远峭深,议者或疑视林为隘,其实不然。夫规模之阔狭,政视其人之意理耳。公<br> 以不贪为旨,则于世俗所趋尚者遗弃不务,专以扩其坚刚之气,兹乃所以成其大也。世之巨公,或纵滥无制,或纷扰无度,自谓宏廓,迹其所营者,裁取惊悦流俗耳目,斯不亦猥琐也哉。味公“夜识”之义,其足愧夫日暮途远钟鸣漏尽之徒,又足以悟君子晚节“戒之在得”之道。昔杨亿谓闽士轻狭,而章得象独深厚有容,知为公辅器。今日轻狭之风盖犹是也,学者必法公之不贪,乃可几于章公之深厚,此则孝胥之持论,未知其果有合于公否也。忍冬藤《本草》亦曰金银花,胥既为之记,仍篆书“夜识”二字遗爱苍,以悬于亭。<br> 与黄遵宪不同的是,郑孝胥在日本似乎不像黄遵宪那样注重考察日本的制度体制的变化。这大概是因为有些个性强悍,喜欢特立独行的人在他们的潜意识层面上不大重视制度规则一类的东西。虽然郑孝胥在日本由于身份的关系,还算是留心口本政局的变化,但是他对日本<br> 明治维新成就的敏感,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制度的考察研究,比较他对中国圣教儒学的陶醉和痴迷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虽然原因复杂,但是对制度维新的忽略,大概是他个性方面的原因之一。<br>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很有趣地说明这一点。1892年8月9日,郑孝胥记了一篇很长的日记。日记一开始,先是用了大约700多字的篇幅写他读《梦溪笔谈》的摘录和体悟。然后又用几句话记录他这一天读到的《日本新闻》中日本政局变化的情况。对郑孝胥而言,日本政局的这次变化不能算是小事,否则就不会在读《梦溪笔谈》时记上这一笔了。然后,郑孝胥又去记录他读《梦溪笔谈》的内容,这段文字大约长达1500多字。这一天,郑孝胥记载他阅读《梦溪笔谈》的文字总量高达2200多个字,但是记录到日本政局变化的内容却只有寥寥几行。通过这篇日记对政局和中国典籍孰轻孰重的态度,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新政和中国传统文化在郑孝胥心目中的不同地位。<br> 因为上述原因,郑孝胥不像康有为、梁启超们那样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的改革维新上,而是放在比较容易见成效的路政、军政和学政上。<br> 纵观辛亥革命以前的郑孝胥,军政似乎对他一直具有不平常的意义。从人幕之前第一次面对张之洞谈论日本以及西方现代常备军的建设,到此后多次建言建立士官学校,制定陆军章程以及作为湖北全省营务处总办和武建军监操官运用西方洋操的新式练兵,再到戊戌变法中向光绪皇帝面奏练兵强国,再到亲自率领湖北新军中的八营武建军5000余人镇守西南边疆,在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与军政改革有着不解之缘。 <br>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在全国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下,在郑孝胥周围那些留学生和其他一些激进分子的影响下,郑孝胥的思想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他不仅主张尽可能早地召开国会,而且主张“删改列国完全之法度”。更为可贵的是,他主张由下议院决定上议院的制度,由法学专家研究各国的法律制度提请国会研究会会员讨论,在充分“各表意见”的基础上,“归于一是”,形成草案。这已经很有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味道了,虽然这个民主肯定是限制在“上等国民”范围之内。<br> 郑孝胥关于预备立宪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他就要通过种种领导手段使之变成预备立宪公会的目标。<br> 6月27日,郑孝胥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后,为预备立宪公会拟定了一份致宪政编查馆的电报,请求速开国会。<br> 在这两份致宪政编查馆的电文和《速成国会草案》中,郑孝胥都强调了召开国会的紧迫性。他所强调的主要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迟疑不决,或者故意拖延,那么“内忧外患”,“乘机并发”,内外敌人,将不会等待我们慢慢地准备立宪。对于这一点不仅郑孝胥、汤寿潜、张謇他们看法一致,持有这种看法的在1908年就有十万人左右,而且这个数字还只是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字的人数。<br> 郑孝胥起草的这些电文中请求速开国会的主张,通过京城官员们的传播,特别是通过当时发行量已经很大的报纸的传播,和当时正在兴起的国会请愿运动中要求速开国会的潮流交汇在一起,形成了1908年夏天国会请愿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同时,郑孝胥和他的同道们的活动,也扩大了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在全国的影响。如前所述,预备立宪公会的核心人物之一雷奋,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在资政院的请求速外开国会提案活动中表现突出,在第一次资政院会议上发言176次,远远超过其他议员的发言次数。而且,雷奋“工于演说,对于院章及议事细则剖析毫芒,闻者称善”。他发言之时,“态度极其从容,言论极其透彻,措词极其清晰而且婉转,等他发言之后,所有极难解决之间题,就得到一个结论,而付之表决了。因此,该院的议员,无论属于民选的,钦派的,一提及雷奋,就异口同声,表示钦佩”。这话虽然出自于雷奋的一个<br> 朋友之口,但是考诸其他材料,此说基本属实。另外一个预备立宪公会的核心人物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大展身手的是孟昭常,孟昭常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上的发言次数为61次,位列前十名之第七,任特任股员的次数则为第二。<br> 第一,他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对清政府的现行政策严重不满,不断地要求维新、改革,但是他们更加相信文化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国家机器的力量。他们认为,如果这些力量在他们手上,改革就会沿着理性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自始至终把目光盯在国家权力的最高层,只注<br> 意运动最高权力机构中的核心人物,主观地放大了朝廷和权要的能量,而忽视了作为国家现代化主体的中下层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考察,他们认为,历史基本上是一些英雄创造的或者说是圣贤精英创造的。在清末时期的中国,人民群众只是一些被教育、被改造、被拯救的对象。叫他们只配被动地接受历史,参与创造历史的资格还不够。<br> 第二,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社会贵族阶层。他们绝大多数都通过科举取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虽然也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荣,但是他们总是把自己摆在天下人的精神导师的高贵地位。他们习惯于社会给予他们的尊贵地位,习惯于享受那种彬彬有礼、井然有序的精神生活。他们期望在他们这些人的教养下成长起一批又一批的社会栋梁,支撑起未来国家的大厦。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由文化精英作导引的社会。这既不是令他们担惊受怕的极端专制的权力社会,也不是令他们感到极端恐惧的无知愚民肆行无忌的暴民社会(这些人对义和团的一致看法是暴民横行,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对义和团的反帝表示同情,但是他们都坚决反对义和团的做法)。无论是改革还是建设,他们都希望在文化精英们设计好了的图纸上有秩序地进行,有条不紊地进行。<br> 第三,从所处的利益格局看,他们是当时社会道统和社会政统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他们显然不希望在他们看来没有受过正统教育(虽然这个正统教育已经在深刻地变化着)的人来重新分配他们既得的精神资源。从郑孝胥对躁进不已的林旭等维新派“新进人士”的鄙夷、批评和爱护,从他对亲自资助留学日本的青年在日本的抗议活动的不满、批评和爱护都可以看出这类文化精英对蔑视社会秩序的人(即使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的矛盾情感。他们虽然在许多情况下能够超越自己的物质利益,不受物质利益的诱惑,但是有时候却很难超越他们自己精神领域的局限。这是文化精英面临的最大问题。当认为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往往是不能容忍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