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鲁士王国的形成
土地和人民
从1415年第一代霍亨索伦人入主勃兰登堡马克以来,到1701年普鲁士王国成立为止,这个家族的每一位选侯,都利用联姻关系、继承协定、巧取豪夺以及其他手段,扩大领土和统治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普鲁士王国是由分布极为广阔的、分散的各部分领土和各种族民集合而成的。
在选侯弗里德里希一世(1414—1440)统治时期,一共才有29 478平方公里土地,包括阿尔特马克(即老马克)、帕里格尼茨、乌克尔马克的大部分、密特尔马克(即中马克),加上西南德意志的老领地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
在选侯弗里德里希二世(1440—1470)统治时期,土地达到39 985平方公里,新增的领土包括:诺伊马克(即新马克);乌克尔马克的部分;通过购买得到的波希米亚采邑科特布斯,派茨,托伊庇茨,贝尔费尔德;通过购买得到的维尔尼格罗德。
在选侯阿尔布雷希特·阿齐勒斯(1470—1486)统治时期,土地面积为42 272平方公里,新增的土地有:通过同波美拉尼亚协定得到的洛克尼茨(1472)和乌尔克马克的维尔拉登(1479);通过卡门茨和约(1482)得到的克罗森、楚里肖、梭默尔费尔德、波贝尔斯贝格,扩大了诺伊马克;另从安斯巴赫继承了一小块领土。
在选侯约翰·西塞罗(1486—1499)统治时期,因家族分家失去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通过购买得到措森。领土总面积为36 353平方公里。
在选侯约阿希姆一世(1499—1535)统治时期,获得鲁坪伯爵领,土地面积为38130平方公里。
在选侯约翰·格奥尔格(1571—1598)统治时期,得到波希米亚采邑贝斯科夫和施托尔可夫,土地总面积为39 413平方公里。
在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1608—1619)统治时期,通过继承(1609)获得西部领地克勒弗公国、拉文斯贝格伯爵领、马尔克伯爵领(包括利姆堡);通过继承获得普鲁士公国。领土面积一下扩大到81 064平方公里。
在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统治时期,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东波美拉尼亚(包括卡敏);马格德堡公国;哈尔贝斯塔特侯国(包括曼斯费尔德一霍亨斯坦因);明登侯国;波兰采邑劳恩堡和布托夫(1657);施维布斯区(1686)。领土总面积已达110 836平方公里,居民人口150万。
在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1688—1713)统治时期,通过继承奥兰治家族领地得到摩尔斯侯国和林根伯爵领(1707);通过购买获得陶罗根和塞雷伊、泰克伦堡伯爵领(1707);通过继承得到诺伊恩堡和瓦伦金(1707);割让施维布斯(1694),土地总面积为112 524平方公里,居民人口165万。
此后诸代普鲁士国王继续保持这种扩张势头。近代德国统一前夕,1866年,普鲁士王国的领土总面积达352 260平方公里,居民人口为37 293 324人。
弗里德里希一世
大选侯创立了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国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他临死前留下的遗嘱中,违背祖宗阿尔布雷希特·阿齐勒斯选侯1473年定的家族法:勃兰登堡马克领地永远不得分割,他把他的国土分配给他的六个儿子。这一大悖常理的遗嘱甚至遭到大科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tz)的非议。莱布尼茨在大选侯去世后简单地写到,这一难以置信的遗嘱在历史面前再次充分表明,不能给予这位死去的选侯以“伟大的”称号。1688年即选侯位的大选侯的次子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Ⅲ,1688—1713),通过各种手段,“打消了”兄弟分割领土的意愿,使大选侯的“最后意愿”未曾实现。
弗里德里希三世出生在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贝格,是一个矮小的、发育不全的“乐天派”,一个好出风头的、爱虚荣的、穷奢极侈挥霍浪费的邦君。他的愿望就是怎样使自己升格为“普鲁士的国王”(即普鲁士地区的国王)。这种愿望由于汉诺威邦的汉诺威家族1692年升格为选侯,并有希望继承英国王位,特别是对手萨克森选侯、韦廷家族的强者奥古斯特,1697年改宗天主教后获得波兰王冠,而受到强烈的刺激。大选侯创立的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国家,其军事力量和版图已不亚于欧洲其他王国。弗里德里希三世以此为后盾,加紧追逐国王王冠。他的这一愿望得到极大多数容克的支持。
辅佐弗里德里希三世的主要大臣,是西部德意志威斯特伐利亚人埃伯哈德·冯·唐克尔曼(EberhardyonDanekelmann,1643—1722)。他从1663年起就是当时王储弗里德里希的太傅,1674年为枢密顾问,1693年被任命为首席大臣和枢密顾问委员会主席,权倾朝野。唐克尔曼为人雄才大略,力图使勃兰登堡一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乃至欧洲的强权,算得上是一代国务活动家。正是在他的辅政下,确保了勃兰登堡一普鲁士领土的统一。他反对选侯的糜费,要求节俭;提倡文化和科学,使勃兰登堡一普鲁士摆脱不文明的状态。他的严格的喀尔文主义特别是他的擅权,引起选侯和其他大臣的不满和疑惧,在宫廷和大臣华滕贝格伯爵的策划下,1697年,他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解职并被逮捕入狱。10年后方获释,虽然恢复了名誉,却不让他再起作用。他曾促成著名的哈勒大学的成立(1694)和促成柏林艺术科学院的成立(1696)。
现在,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可以毫无顾忌地充分享受父亲大选侯留下的产业。他也继承了大选侯晚年执行的政策:站在德意志帝国皇帝方面,为皇帝效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同皇帝长时间讨价还价后,达成这样一桩交易:选侯允诺在未来的战争中出租8 000人的勃兰登堡军队供皇帝使用(稍后皇帝把这支军队投入反对法国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人员伤亡殆尽),皇帝则付给他“补助费”1 300万塔勒的巨款,同时皇帝还承认他为“普鲁士的国王’,作为酬报。选侯用他的臣民的鲜血为代价,在从前德意志骑士团拓殖的威塞河和梅美尔河之间的普鲁士公国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王国。从弗里德里希三世方面说,国王的新头衔意味着霍亨索伦家族追求的世界地位和强权,其客观意义完全超过了对个人虚荣心的满足。从德意志帝国方面说,出身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莱奥波德一世皇帝及其后继者们,根本没有想到德意志兰东部边陲地区的“化外”家族,会因此而成为自己苦涩的对手和继承者,并最终把自己从德意志排挤出去。
宗教宽容与犹太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一位开明的宗教宽容者。在普鲁士这个新教国度,所有新旧教教派和教徒都获得安全的地位。原因不仅仅在于霍亨索伦家族君主有这样的传统,更重要的还在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是个不信神的人,他不是教徒,他认为自己是凌驾于所有教派之上的世俗君主。就凭这一点当时就已经够惊世骇俗的了。而从弗里德里希二世看来,“宗教宽容”无非是一个给普鲁士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世俗问题”,而不再是什么“宗教问题”。1740年6月22日,在他即位后不久,他的大臣请示,是否为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士兵的孩子在柏林建立学校?这在当时是一种“不合习俗的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请示上批道:“宗教必须完全宽容。财政官员必须看到,这样做不会损及任何人,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可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升入天国。”29年后的1769年,这位具有“宽容”思想的国王很有意思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即“宗教永属国民”,当然只能有利于国家:“按农村学校的意图,必须设法让农民和村民的子女接受宗教课,使他们更加通情达理,教他们正确地理解他们的义务。”
在“弗里茨时代”,“宗教宽容”确实主要是一个世俗的经济问题,一个争取移民的问题。在一种受到国家鼓励的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国家有利的移民(难民)迁居中,普鲁士政府并不过问来人的国籍和教派,它只是考虑,它能得到什么利益。普鲁士的移民(难民),几乎来自欧洲所有国家和地区:一小部分来自俄国和乌克兰、波兰和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瑞典和芬兰分裂出来的教派;有一部分不知国籍的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到处都有为数众多的胡格诺教徒和瓦隆人,他们来自法国和西南德意志兰;还有一些瑞土人和列支敦士登人、卢森堡人、荷兰人、丹麦人、英国人,加上不少南德意志人。当时的南德意志兰,还处在天主教的“不宽容”统治之下。总计在“弗里茨时代”,约有30万人迁入普鲁士,其中10万人在库尔马克(即勃兰登堡马克选侯领),约2万人在马格德堡地区,1.5万人在东普鲁土,1.2万人在西普鲁士,约2.5万人在波美拉尼亚、诺伊马克以及西部省份,还有6万多人迁入新获得的省份西里西亚。
在首都柏林,有大量外国移民和移民区,其中法国移民最多,也得到“崇法者”弗里德里希二世最多的优待,他们越来越被“同化”为“地道的柏林人”。法国的文化和语言不仅影响而且部分融入柏林的文化和语言。弗里德里希二世优先选择法国人或法国难民的后裔作同伴、朋友、顾问和大臣,他实际上经常处在法国人的包围之中。柏林移民中占第二位的是犹太人,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去世时,柏林犹太人已有4 000多,他们在语言、衣着、风俗习惯方面也受到了“同化”,然而由于犹太教徒同基督教徒之间禁止通婚,犹太人改宗为基督徒的尚属少见,双方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宗教成见,还谈不上同柏林市民之间的融合。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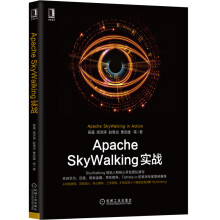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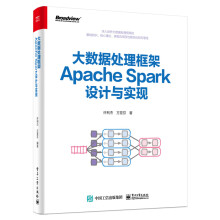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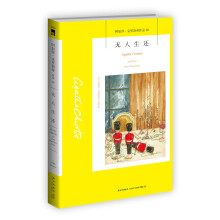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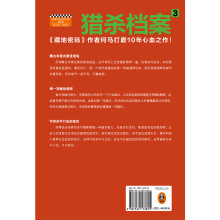
作为政治地理概念,普鲁士有三个含义:第一,中世纪曾在德意志骑士团统治下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人领土;第二,1701—1918年在德意志霍亭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它足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联邦内的一个邦国;第三,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覆灭后所设的德国的邦种意义上我们了解到,普鲁土足一个德意志国家,一个德意志邦图。
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领土的、历史的、精神的、文化的延续性。第一个含义和第三个含义只能列为附带说说的“前史”和“后史”,真正充当德国历史上正经角色的,是1701年到1918年的普鲁士三国。人们很难想象到,普鲁士是从一个小小的、荒蛮的、穷困的东部边区马克”,一个被人轻蔑地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第一帝国)的砂石罐头”发展起来的。在不到五个世纪内,普鲁士成为德国的绝对领袖,欧洲的强权,争霸世界的庞然大物(德意志第二帝国),叱咤风云于欧洲和世界。在每一次涉及到疆土的关键时刻,普鲁士的君王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进行战争。普鲁士就像一尊冷酷的“战神”,手握条顿剑,在行动。普鲁士这种过度“武化”的自我膨胀,最终导致自己的被消灭,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显而易见。在历史上,普鲁士问题是一个德国问题,一个欧洲问题,乃至一个世界问题。而令人惊奇的是,在现实中,普鲁士问题也依然经常若隐若现地作为一个德国问题、欧洲问题乃至世界问题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想探索的“什么是普鲁士”中的深一层问题:普鲁士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有着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和传统。
普鲁士现在早已不存在了。人们对“普鲁士”的记忆和了解,都已相当淡化和模糊,完全不像在19世纪德国统一前后多数德国人对它的崇敬。1864年,普鲁士历史学家亨利希·冯·特赖赤克说:普鲁士“这个国家,是我们人民最伟大的政治业绩”。这话是颇具代表性的。更不
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世人对它抱有某种“深仇大恨”,乃至“谈虎色变”,非欲置死地不可。1943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说:“我想强调,普鲁士是万恶之源。”他显然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和纳粹暴行归之于普鲁士。苏联红军在向柏林进军时,奉命彻底摧毁德国东部土地上普鲁士容克的庄园,乃至铲除窖克的祖茔(像俾斯麦家族的)。当希特勒帝国整个被摧垮后,1947年2月.战胜国在德国建立的最高机关“盟国管制委员会”公布第4号通令,用英语、法语、俄语以及适用于被战胜者的德语向全世界宣告:“普鲁士
邦,它的中央政府和属下所有官厅至此全行解散。”这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措施,因为自此以后,“万恶之源”的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一个邦国,一个邦,真的从欧洲政治和世界历史中“无声无息地沉向地狱”,消失了。
但是,在今日世界的现实中,却依然存在着众多的“普鲁士人”和·普鲁士物”。苦鲁士的精神、文化和传统,并不能光靠行政手段予以消灭。在战后的联邦德国,以及建立在前昔鲁士中心地区勃兰登堡土地上的民主德国,特别是那些割让给波兰和苏联的大片东部土地上,时时有“普鲁士的幽灵”出没。德国人是绝对摆脱不了作为历史现象的“普鲁士”的,无论是民族主义也罢,民主—自由主义也罢,也无论是国际主义也罢。上世纪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历史学界首先发难,翻“普鲁士是万恶之源”的案。塞巴斯提安·哈夫纳和乌尔利希·威廉特合撰了《并非神话的普鲁士》,提出普鲁士并非因其“军国主义”而威胁邻国,普鲁土只是由于它的“廉洁的管理机构和独立的司法,宽容的宗教和开明的教育”而使其邻国深感不安;“普鲁士在其古典时期--18世纪是欧洲最新式的和现代化的国家”,它比欧洲的任何国家更“富有远见”,古典普鲁士是纯粹理性甲家;为把分散的地区连为一体,要求它比其他国家更应成为一个军事国家云云。贝尔恩·恩格尔曼在其著作《普鲁士——一块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国土》中认为,普鲁士应该理解为“兵营和自由圣地的结合”,它是“统一德国的先锋”,具有“无条件履行自己的职责、全然正确和自由开明的理性国家”。1979年第二期《明镜周报》刊载赫尔穆特,古姆纽尔专评上述两书的文章《普鲁士是万恶之源吗?》,点明了问题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