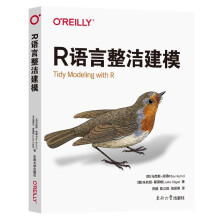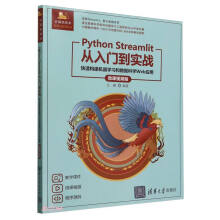周氏兄弟的里与外
孙郁
有一次张中行先生对我说,鲁迅和周作人的区别是,一个趋于信,一个止于疑。初听此话,我诧异了半天,虽然不能全部信服,但觉得还是讲出了些道理的。我的不能全部苟同张氏的观点在于,其实内心也隐隐认为,鲁迅也是个多疑的人,并不像人们看的那么简单,归于了什么信仰。在我的看法里,两人一个守于象牙塔里,一个在书斋之外。起初好像在一个起点上,后来各自东西了。有趣的是,这一里一外,看似有别,但他们在一些地方却做着相同的工作,如果从史的眼光看,构成了新文化的合力,没有任何一方,都是不行的。
以对日本文学的态度而言,周氏兄弟在许多地方意见是一致的。1923年6月,他们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收有夏目漱石、森鸥外、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菊池宽、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人的作品。周氏兄弟对上述诸人的作品是喜爱的。夏目的机智从容,有岛武郎的悲悯,芥川的幽默哀婉,我们在中国的小说家里尚未见到。他们急切地介绍这些,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至少说是想让国人得到一点启示,小说还可以这样来写!此后他们依然不断地注意岛国里的艺术,时常将这些转换到自己的思想里。不过两人这时出现了一种差异,鲁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现手法,用自己的创作呼应着文学里的写实精神和个性精神。周作人则从学术的层面阐发独异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的意义。后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前者乃外面世界里的耕耘。彼此的兴奋点各自有别了。
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对这个国度的文学有独特的阐述,资料与观点殊为精妙。周氏谈自然主义与写实派的小说,多有会心处,一看就是深味文学内蕴的人,文中有不凡之气。我读这篇论文,很是佩服作者的眼光,他能从人性和新的审美的角度看日本文学的新风景,可说站在了与日本作家同样的高度上,丝毫没有排斥的心理。勾勒小说的特质时,又能有史家的气度,仿佛是个日本的批评家。但周氏并不是就日本来谈日本的,目的是批评中国文学的不发达,用此引起世人的注意。文章的结尾写道:
讲到中国近来新小说的发达,与日本比较,可以看出几处异同,很有研究的价值。中国以前作小说,本也是一种“下劣贱业”,向来没人看重。到了庚子——十九世纪的末一年——以后,《清议》、《新民》各报出来,梁任公才讲起《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随后刊行《新小说》,这可算是一大改革运动,恰与明治初年的情形相似。即如《佳人之奇遇》,《经国美谈》诸书,俱在那时译出,登在《清议报》上。《新小说》中梁任公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是政治小说。
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旧派小说还出几种,新文学的小说就一本也没有,创作一面,姑且不论也罢,即如翻译,也是如此……我们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脱化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写这篇论文时,鲁迅和周作人正生活在一起,观点是相近的。奇怪的是鲁迅没有发表这样的论述,而是默默无闻地在从事着模仿与创造,那时就有了《狂人日记》的出现。小说明显是模仿了果戈理和安特莱夫的某些篇章。通篇并不幼稚,按严家炎先生的观点说,现代中国小说,在他那里开始,也从他那里成熟。周作人企盼的新小说,可以说在其兄的劳作里出现了。
从理论上自觉地思考一个问题是一种境界,思考后不是把它放在书架上,而是将其变为改变世界的冲动,将其物化在曾是盲点的地带,那是更高的境界。鲁迅远远地走在前面,把我们这些俗人甩在身后,现在大概还没有人追得上他。
因为知道木山英雄先生是周氏兄弟研究的专家,我曾特地向他询问过一些材料。20世纪50年代他去访问羽太重久,了解周氏兄弟的情况。羽太说,鲁迅见到人时很热情,善谈,给人亲切之感。周作人则不太爱讲话,陌生人不好与之交往。这也证实了我过去的猜测,鲁迅有趣,幽默而有性情,周氏则缺少与尘世周旋的机智,于是只好退回到书斋里吧。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反映看,鲁迅适宜去做拓展空间的实事,将愿望落到实处,周作人至多不过是务虚的思考者,描描天气,说说掌故,和田问的劳作者是没有关系的。我看两个人的特点,觉得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谧的。后来的文学,是沿着两人不同的道路分离开的。
谁都知道,鲁迅和周作人是民俗学的提倡者。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建立与两人关系甚密。周作人是理论上的建设者,一生力介弗雷泽、安特路朗、蔼理斯的理论,以为在民间的土壤里,才有文化的本源。中国的正宗文化是官的文化,不过是权力者意志的体现,可吸取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点,有时等于通篇废话。但我们到乡间去,那些口头传说、歌谣、戏曲则有诸多美妙的情调,周作人在风俗与传说里看见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这正是旧式文人不注意的内容。你看他谈风土、神话时的兴致,好似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因为那里隐含的正是集体无意识的东西。研究文化,就不能不关顾这些。我注意到他多年来潜心于此的耐力,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民俗学的学者涌现了出来,其功不在一般文人之下。而鲁迅不同的是,深知问题的重要之后,却在创作上下功夫,在小说和随感里展示着精神里的景观。我有时对照两人的文字,不禁会心一笑。周作人强调的文化人类学的隐喻,在鲁迅那里竞出现了。文本中折射的谣俗因素颇多,现代小说家中他是第一个民间风景的打量者。
谈狐说鬼在一些人眼里乃旁门左道,抑或堕落云云。周氏兄弟却偏偏喜欢这样。只不过一个从学理上引经据典,一个将此外化到文学的画面上来。在学理上,周氏的眼光我们有时不能不佩服,他对那些西洋人的著述颇为了解,每每有新奇的发现。他经由安特路朗进入神话及社会人类学,发现民风大多是古代蛮风的遗传,今人身上还留有远古的习俗。人就生活在这样的历史的影子里。了解自我,有时就不得不往古里找找原因。鲁迅的看法与此接近,他不在理论的层面理解这个问题,而是从实际观察里得出结论,在形象可感的画面里,昭示着历史的投影。他写故乡的鬼气,阴魂里的咒语,我觉得比任何一个中国的民俗学者都要高明。那里浓缩着诸多意绪。对社会和旧时代的解析,不仅令人生叹,重要的在于,也给研究者留下了思想的空间。周作人晚年为鲁迅小说写注解式的文字,倒是说明了这一点。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