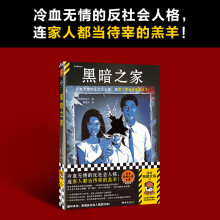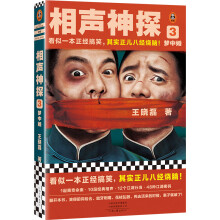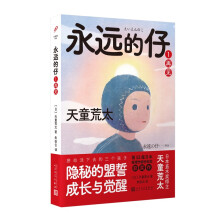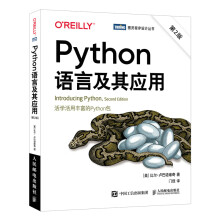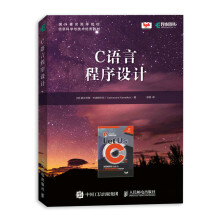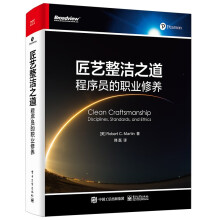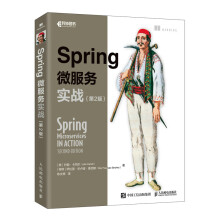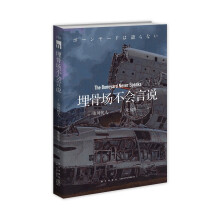论述至此,以北朝君王对于胡乐的耽玩好尚及胡人乐工的贵盛得意为线索,“繁手淫声,争新哀怨”的胡乐,寝寝然已凌驾中国音乐之上,由此蔚成风潮,成为流行音乐的大宗,试观《旧唐书·音乐志》的记述:
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此处所谓“杂曲”,应是指北方俗乐。数百曲俗乐调,非西凉即龟兹,可见其普遍流行,大量“倾销”之一般;而其曲度皆时俗所知,又可以见其广受欢迎,浸润人心之深。“以胡人俗”在此已经得到了最佳的印证了。
(三)以俗入雅
上文是“以胡人俗”、“以胡人雅”两种现象的论述,而“以俗入雅”又是音乐发展的另一脉。“以俗入雅”的情形早在北魏已有之,试观《魏书·乐志》二例:
(太祖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北魏拓跋硅时代,一方面创制了“真人代歌”,另一方面,“宫悬正乐”中还要兼奏“燕赵秦吴”、“五方殊俗”之曲,并用于“四时飨会”之中,这正是因为雅乐陵替,所以只好吸收民间俗乐以滥竽充数。魏孝文帝锐意汉化,试图正乐,充实雅乐的内容,结果也是一场徒劳无功,更泄露了当时太乐中颇多“方乐”及“四夷歌舞”的事实,可见“以俗人雅”、“以胡入雅”在当时都是不足为奇的了。
江南之地,虽然胡风点染不如北方之甚,对于所有雅乐宫悬的保存使用,也远较北朝为严谨,但是南朝之乐并非始终一成不变,其内在变迁的脉络仍可一一寻索。“以俗人雅”正是南朝音乐发展的主脉。《南史》卷二二《王僧虔传》便载僧虔“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人间竞造新声”,上书请正声乐一事,《宋书》卷十九《乐志》收有王僧虔这封奏议,其论雅乐曰:
今总章旧佾二八之流,挂服既殊,曲律亦异,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大明中,即以宫县合和*、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
僧虔所论,证明南朝雅乐也代有变异,挂服、曲律均有不同;并且以俗乐的稗舞、拂舞人于宫悬乐舞之中,更说明了南朝亦不能逃于“以俗人雅”的发展规律。在俗乐方面,南朝向来以清商最为大宗,更是不能免于南方谣俗的影响,王僧虔于此也有议论,《宋书》载其言曰:
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焦危,不顾纪律,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由此可见,所谓“新哇”、“谣俗”是清商变迁的主因。《旧唐书·音乐志》曾追述清商的渊源发展曰:
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清商虽是汉末以来的“遗声旧制”,但“散落江左”之后,亦是“世有新声”,此处说明了清商也由新环境中汲取了新的滋养。此外,南朝君主之中,耽好音乐者亦不乏其人,如陈后主,《隋书·音乐志》称其“尤重声乐”,多制新曲,“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再如笃信佛法的梁武帝,也曾制《善哉》、《大乐》等佛曲。因此,南朝俗乐的变化也是相当可观的。
“以俗入雅”的著例出现在隋代。隋文帝继承了北周的基础,一统中国,对于江南风土,无比向慕,以为南朝所传,均是“华夏正声”。《旧唐书·音乐志》曰:
开皇九年平陈,始获江左旧工及四悬乐器,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隋世始有雅乐,因置清商署以掌之。……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而已。隋末大乱,其音犹存。开皇九年,隋平陈,诏于太常寺之下,于原有的太乐署之外另立一“清商署”,负责处理保存南朝旧乐。《通典》卷一四一曰:
隋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盖采此为名。求得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所谓“盖采此为名”,意即虽采用了清商之名,而实际内容包括了
宋齐旧乐”,不止于清商俗乐,可知隋代“清商署”的内容兼含了雅乐宫悬的“四悬乐器”。
隋文帝叹美“华夏正声”并设立“清商署”的举措,可谓“以俗人雅”的典范。顾名思义,“清商署”本应掌理清商俗乐,但隋代以清商署作为“雅音”的代表,并说是自兹而后“隋世始有雅妻”,在名义上已将“清商”视为“雅乐”了。由内涵上看,隋代的“清商署”雅俗兼收,所收的是代有变异的雅乐和屡传新声的清商。这些雅乐早已经历世变,恐怕较王僧虔所大肆抨击的宋代雅乐更“有乖雅体”。至于清商俗乐,不仅包括了“新哇谣俗”的江南新声,也有陈后主新造的《玉树后庭花》之类“极于轻薄”的清乐,因而祖孝孙评曰:“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并非无的放矢之论。此一雅俗淆杂的“清商署”,非但为隋人备极推崇,并且被文帝许为“华夏正声”,列在太乐,目为隋世雅音,“以俗人雅”,莫此为甚。
本章检视了永嘉以下,迄于隋唐之间二百八十余年间的音乐大势,此一时期内,雅、胡、俗三乐急遽交化,雅乐沦丧既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因而出现了三条发展脉络:其一是以胡入俗,其二是以胡人雅,其三是以俗人雅。证诸史籍,北朝以熏习胡风,“以胡入俗”、“以胡入雅”的情形均较南朝为烈;南朝则杂用南声,常有“以俗入雅”之事例。胡乐在此时大举进人中国,其声势令人瞩目。但经由以上的考论,可以见出北朝对于胡乐的吸收,除了政治的考量安排之外,也是“乐操土风”的自然需求。经过这三百年音乐资源的汇聚,此后所急需的,是整理融会的工夫,是反省深思的熔练,而要成就此一大工程,还有赖于气势恢宏,心胸开阔的大环境。《新唐书·礼乐志》评论唐以前的音乐发展,谓“稍欲有作,而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的确是一针见血,切中肯綮之论;唯务争伐,割据一方,而又气局褊狭的君主,是无法成就文化艺术上的丰功伟业的。唐代社会既有开放的外在氛围,又继承了三百年的音乐资源,因而唐代音乐如鹏搏九霄,一发不可遏止,终于成就了姿彩缤纷,光彩烂然的音乐盛世;回溯其背景,有赖于音乐史内部的自然发展和外在社会环境的同时促成,岂是偶然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