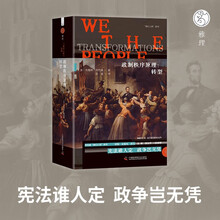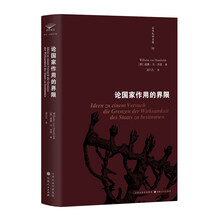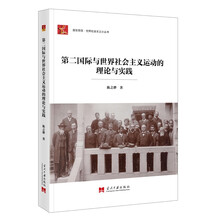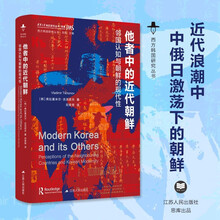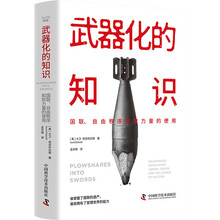从某种过于抽象的高度去批判自由主义,有可能是不得要领的。首先,从那些关于人的价值之本质的深奥哲学,跳到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论断,这样做毕竟有一定危险。——价值也许是主观的武断,带有工具理性的特点,而个人却还可以是互相依赖或高度社会化的。自由主义首先并不是关于“自我与自我之目的”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它直接提供的是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这种方式重视自由、个人权利、法律、有限政府以及公众理性等的重要性。当然,要理解“自由主义名下那些常常是异质混杂的”思想与主张,有很多途径可循,其中一个可靠的途径就是,寻找那些与公认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与实践相关的人格及理性能力的特征。
自由主义认为,具有理性能力的人正当地追求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目标、理想及事业。实际上,自由主义政治学及其人性论的一个了不起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把人从那些束缚个体并限制选择的世袭角色、固定等级以及习俗中解放了出来。自由主义的理性能力必须足够广泛,以兼容并蓄;它必须容纳自由主义多样性、公众理性,以及针对个人的角色及效忠义务的批评性反思。
在排斥工具论时,一些社群主义者表现出某种怀旧之情,他们想回到以前的社会,在那里,政治权威决定什么是好的生活。他们似乎认为自己知道人性的善究竟是什么,但又语焉不详。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关于公共的或客观的善的信念,应该劝导人们远离自由主义。毕竟,好的生活与人的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用麦金太尔的话说,美好生活就是“用来追求人的美好生活的生活”。宽容、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社群恰恰为探索各种改善生活的方式提供了空间。言论、出版、交友、旅行、旨趣相投的成人之间私密关系的隐私安全等自由主义权利,都保护人们在同等尊重他人权利的前提下去寻找好的生活。
我这里所辩护的自由主义学说认为,个人自由是政治的核心,并且通常情况下,权利高于对公共利益的集体追求。这种优先性并不以价值主观主义或者对人性的善的怀疑论为基础(这一点应当阐明),也不以对理性的工具化理解为前提。自由主义假定,只要具有反思能力,能制定生活计划、行为正这一事实稳定了我们的思考,为选择提供了初始基础,即,思考的相对稳定的起点。正如泰勒所言,我们的描述“并非简单的武断,并非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些事情是或多或少注定了的,比如,我们不能选择父母,不可能永生,不能逃税(尽管对于这些带有明显“强制”特征的限制,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姿态、作不同的理解)。对于某些习惯的推论、信仰以及性情,不论是批评性地考察还是再造,都是很困难的;而其中有一些如果要放弃而又不造成精神痛苦或者导致“认同危机”,就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重视那些由特定性格导致的限制外,我们重视整体性,行动的某种一致性,至少是统一性或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之间的关联,或者如麦金太尔所称的,它是关于好的生活的“叙述统一体”。
个人的人格为选择提供了暂时性的基线,我们从自身所在的位置出发,而不可能没有出发点;沿途我们还有其他不太个人化的路标。用丰富的评价语言去言说现存的困境,就是调用各种价值观,使之充当我们这样或那样行动的理由。一个自治的个人将“根据从自身传统的某个方面得出的批评准绳,去评判其传统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武断地运用学到的观念(如果我们学到了的话),也不能用自己想要的东西去任意塑造我们的情境。我们可以有想象力地臆造一些选项,但我们仍是自身情境的批评性解释者,以及各种评价标准的有鉴别力的继承者。
我们凭借公共道德语言,去理解自己业已形成的身份以及现有的各种选项。没有人能超越这种语言,不管霍布斯、“胖蛋先生”’这类主观主义者们曾经怎么想。道德词汇与范式所包含的意义,并不总能等于我们希望它们能包含的意义。泰勒指出:“总有较充分或较不充分、较真实或较不真实的……解释。……言语会出错。”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可能误解自己的倾向,还因为一个人对于理想、价值以及善领会得不够充分、不够清晰——那些理想、价值以及善不只是他个人的,也不是由新的个人、新的一代所臆想出来的。
自我解释与自我批评应当包含对高贵与平凡、勇敢与怯懦、成功与失败,以及对信任、友谊等观念的审视——不仅是“向内”看,而且是“向外”看。指引我们的,不仅有各种关于我们自身性格的新颖见解,还有各种公共理念,后者天然构成一个人最为个性化的抱负的源头与模型;它们总能被创造性地个人化,而非一味地模仿。
作为道德主体,公民认识到追求自由主义正义乃是一项至高无上的事业,他们都具有道德上的自我批评能力;并且他们承认,自由主义正义调和每个人的自由与全体人的自由,如果自己的目标与计划不能通过这一非个人性标准的检验,那么它们就必须得到修正,甚至被毁弃。但是,自由主义正义的那些理由,不是强加给自由主义公民的外在要求。正义不仅是一条检验我们行为的公共标准,而且,在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里,还是自由主义公民的生活的构成性特征,它从一开始就塑造着公民的目标与志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