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见一个 批一个
不快乐 你有罪
在我的价值观里,崇高一向是排第一的。比如我曾经一心想解放全世界。这事儿无比崇高,但我完全没有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以及世界究竟接不接受我去解放等问题,结果这个失了理性之基的崇高,至今还没着没落,它也就只能在我的心里越埋越深。如果不暂时忘却这个崇高,我就会沉浸在永久的痛苦里。现在我终于不崇高了,这虽然不可喜,但它锻炼了我的判断能力,比如当发现大家一般认为痛苦比快乐深刻时,我立刻发现它是一个假命题。
崇高,简单说来就是愿意为别人做出牺牲,可惜知道是一回事,做到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虽然高喊崇高的人很多,但其中大部分人很难达到这种高度,崇高也就变成了他们的口头税——嘴上交过了完事。有鉴于此,我尊重崇高,但希望大伙们还是先做好遵纪守法什么的,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向崇高。
崇高是为别人做牺牲。为别人的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别人快活。挑剔说来,自己不快活让别人快活,这有低估别人觉悟的嫌疑。既然大家都快活更好,那么快活可以被看作是崇高的一项基层工作、群众工作。那就想办法让大家都快活起来,这个“大家”里有别人,也有自己。雷锋能让别人快乐,他自己也很快乐。我们学了五十年雷锋,雷锋总数还是不够多。难道大家都希望别人是雷锋而自己被雷锋吗?我看还是自己先成为雷锋好。让自己成为雷锋的标准太高,那就先让自己快乐点儿,大家都快乐了,有雷锋固然好,没有雷锋问题也不大。
现在我不够崇高,也没当上雷锋,我并不以此为荣,但也并不以此为耻,所以我只能说说我自己。事实上我不愿意别人为我做牺牲,那样我会很痛苦。从小我就遭遇过各种各样的“老师”,假如老师已经崇高了,他要求我崇高,那么我会努力争取,争取不上去,我只能红着脸说“请假以时日”。假如老师不崇高而要求我崇高,我则连交口头税的愿望也没有。曾经有一位“老师”发现我比他快乐而怒火中烧,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想方设法整理我,明摆着原因就是“你凭什么比我还快乐!”这个人平时讲起崇高来头头是道、无比动人,其实正是他败坏了崇高的好名声。给他讲理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在他的眼里,我的理不可能比他们的理更正确,再说了,他也一定认为我的下属身份还不够格给他讲理。
另一个事实是,我是个文人,或者说是个业余文人,没正经学过理科,不能像王小波那样,文理双辉。所以我发发牢骚一般来说还是可以的,但让我讲理,常常是力不从心。但我现在很羡慕理科,羡慕理性,渴望道理。我希望通过发牢骚能说出点道理来,假如你能从我的牢骚里读出点道理来,我一定高念一声阿弥陀佛。
我不清楚一根草冒出芽来的意义,也不了解一只蚂蚁东奔西走是不是很快乐。作为一个人,各种信息告诉我:一定要争取活得有意义一些。但这些“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总是不甚了了,甚至越来越迷糊。所以我宁愿相信一个被人认为是“浅薄”的人生意义——那就是快乐,或者说获取快乐。基于这种浅薄,我活得看上去很不成样子——活像是一枚单薄的树叶,二两轻风,就能把我吹向云边。上班见到树上的黑白喜鹊,会让我持续高兴相当长的时间,就算出门看见乌鸦,也是极高兴的,在我眼里,乌鸦一身黑衣酷得很呢。有时候我甚至异想——乌鸦是不是喜鹊化装来的呢——把白毛染成黑毛,不是难事,人间也很流行。
显然,我的快乐还不够纯粹,甚至很主观。比如我要写下这些文字,就是试图向别人证实点儿什么,或者说有点儿企图,比如企图通过“以文会友”,找到一两个浅薄的同党。好在这事儿没有犯法,也不算犯罪。总之,无法获取快乐,被我认为是对人生的重要犯罪。
当一个人第一次对你奉上红苹果般笑脸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有点傻X;当他第二次对你奉上红苹果般笑脸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有些怪;当他第三次对你奉上红苹果般笑脸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有病”。但是,当他第四次、第五次对你奉上笑脸的时候,估计你已经开始骨碌着眼珠儿犯嘀咕了:他又不是苹果专业户,一张脸咋就整天红彤彤乐呵呵呢?这个嘀咕还没有结束,你还会开始打量自己,嘀咕到自己身上来了:我怎么就不快乐?到底是人家有病还是我有病?
拿破仑对圣海莲娜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就没有真正快乐地过过一天”。我想如果拿破仑某一天真的拿个破轮子,敞胸露怀,迎着小风,在大路上玩上一遭“推铁环”,说不定他会乐不可支。宋代有一个叫范仲淹的古人,在我看来,实在是思想先进得了不得,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过,在我看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很好,后天下之乐而乐嘛,倒也不必,都等着别人乐完了再乐,情况似乎比较奇怪,能与民同乐就可以了。
在我周围,有很多优秀人士,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这让我很感动。比如他们忧虑情侣在街头接吻影响儿童身心,忧虑出门吃饭传染SARS,忧虑一不留神放了个响屁影响自身形象,他们忧虑街头姑娘们不要脸,我也忧虑。但他们若提议“让姑娘们回到闺房去绣花,去等待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就会投反对票。
因为在中国人中间生活,对他们很多人的快乐我有所理解。他们对人生快乐,原先有两个结论:一是当官,二是生儿子。现在又多了一个字:钱。殊不知这三个东西各有各的局限性,最重要的是它不是快乐本身,对于快乐,它们都是外因、都是末。他们认为这三个东西等于人生、等于人生快乐。本来我也没意见,但他们非要以己推人、以此判人、以此教人,就让人无比难受。有一个忧虑我深有体会,本人一个奔四十的人了,还没打算生个孩子养着,很多人就用忧心忡忡的眼神“先我之忧而忧”:忧虑我“脱离群众”一定很痛苦,甚至忧虑俺们老王家的香火,忧虑俺回老家后会挨老爷子的烟袋锅子。总之,我的快乐,在他们眼里是不成立的,我的哈哈大笑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装出来的,我的胡吃海喝是掩饰痛苦、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我的“活着”是大大地没意义的。除非俺也像他们一样到点儿就娶个媳妇,到下一点儿再整个孩子,否则俺的快乐就无法说服他们。好在我已经不想说服他们了。我不是鱼,我是我,我自己的快乐只有自己知道。当然,没有孩子的俺,如果能让有孩子的他们当做嘲笑的标本,能让他们的“活着”更加意义非凡、快乐无边,我也是高兴的,有生之年总算对广大群众做了点儿意外贡献。
显然,快乐不一定都是客观赐予的。上帝自己说不定也不快乐呢,又没有比上帝更大的头衔引诱他“夙夜在公”,他哪有劲头天天普度众生——挥汗如雨地往大家伙儿的后脑勺上丢馅饼?快乐有时候就像欧洲球迷脸上的五色油彩,是需要自己往上涂抹的。快乐缘于精神,精神很大程度上来自主观。在快乐的问题上,主观主义的“强加”似乎也是行得通的。我看到一个台湾什么公司的“大忽悠”,把一帮年轻人拉到大街上锻炼“公关”,半天的功夫,那帮瘪脸窝脖的年轻人还真变成了精神抖擞、热情洋溢。结果不但自己兴高采烈,连围观的群众都兴致勃勃起来。倒是一个骑车路过的楞小伙高声赞道“牛×!”,然后在大家的笑骂声中乐呵呵狼狈逃窜,几乎带乐了三十多米长的一条大街!
当年李银河从国务院调到社科院,被很多人认为是“傻子行为”。王小波说“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你是傻瓜,唯独我不会,我爱你。”这句话我多少有些感动。我琢磨着李银河一定认为“调到社科院搞研究”是快乐的。这就是说,快乐不一定是随大溜。尽管不随大溜容易受到攻击,好在王小波又说,沉默胜于一切解释。我想他是有道理的,因为我除了知道自己如何才能快乐之外,并不知道如何也能让别人快乐,比如我觉得来到网上论坛很快乐,我就不能召集我的部队说“同志们,快去网上论坛吧,那里有你们寻找的快乐!”如果我这样说,那帮小伙子一定背地里为我诊病。
我一直怀疑自己在网上晃荡的目的,怀疑自己写网络文章是不是为了一份小小的“虚荣心”。唯一能找到的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就是自以为自己狗熊的包袱里,似乎揣着几只快乐的玉米棒子,或者还有一份善良的企图,那就是能同一些天涯海角的人共享那些快乐的颗粒。哪怕是一些展示痛苦的丝穗,不也是因为我们心存一份剥离它于尘埃的妄想?网络显然不可能通往极乐世界,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是不是离极乐世界近几个厘米呢?
是的,我可以沉默,但我必须找到自己的快乐。你可以跟我不一样,但你不快乐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存在。当然,我也没有资格给不快乐的你定罪,更不能给你量刑,所以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让自己快乐些。那就开始吧,从现在开始。快乐也不是慢乐,更不是跟在别人屁股上乐——哪怕那个屁股是上帝或者上帝夫人的。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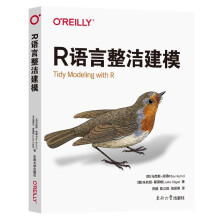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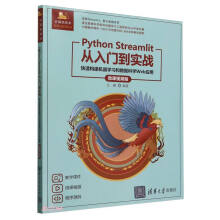


——摘自网友“狼之独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