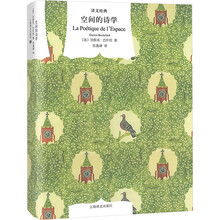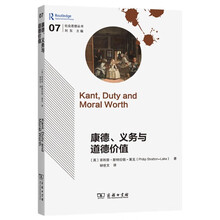适合我的营养和气候<br> 为什么我知道得比别人多?换句话说,为什么我这样聪明?这是因为,我从来不去思考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从来不去浪费自己的精力。例如,我从未体验过宗教方面的难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是“有罪的”。同样,我也不明白“悔恨”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悔恨”这种良心发现是不值得重视的。我做事从不后悔。我做事要考虑到价值,尽量避免不好的后果。而造成恶果后,人们往往不能正确看待自己做的事情。在我看来,悔恨是一种“邪恶之眼”;有些事情,正因为它造成的后果不太好,我们更应该去维护它,这样才符合我的道德观。“上帝”、“灵魂不朽”、“拯救”、“来世”,这都只是一些观念,而我对这些观念根本不加注意,从来没有为它们花费时间,甚至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就是这样——也许在这一方面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我对无神论的了解,并非是作为某个事情的结果,而是出于我的本性。我生性好奇,太爱怀疑,过于自负,因此,任何简单粗略的回答都不会让我满意。对于我们思想家来说,上帝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粗略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上帝只是对我们下达了一道粗暴的命令:你们不许思考!<br> 我对营养问题更感兴趣,我认为它在拯救人类方面要比任何一种神学奇迹都更重要。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提问题:为了获取最大的力量,为了摆脱道德教条的束缚,我们应该怎样注意培养自己?在这一方面,我个人的体验糟透了,因为过了那么长时间我才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德国的文化毫无价值,它所提倡的理想主义,也许可以解释我在这一方面为什么如此迟钝。这种文化一直要求我们忽视现实,去追求那些所谓的理想目标,而它们本来是应该被怀疑的。应该承认,直到年纪很大,我吃的食物都是十分糟糕的。而厨师和其他基督教同伙则将其称为“无个性化”、“无我”、“利他”的食物。如果要把一个人弄成营养不良者并破坏他的胃,这种食物就足以达到这一目的。德国人的烹饪有些什么东西?——16世纪威尼斯食谱所谓的餐前汤,煮得索然无味的肉,将油脂和面粉混在一起煮的蔬菜,已经变质变硬的面点。此外,在正餐后还要大量吃肉,不仅古人,现代德国人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知道德国人的智力为什么这么差劲了:由于这种有病的肠胃,我们可以说,德国人的智力是“消化不良”的,无法消化任何东西。英国的饮食跟德国、法国不一样,有一种返回自然,也就是返回野蛮状态的味道。但它还是不太适合于我的本性。对我来说,最好的烹饪应该是彼特蒙的。我不能喝酒;只要喝上一杯,就会打乱我一整天的生活。而住在慕尼黑的人,情况跟我正好相反。我很小就认定,喝酒抽烟不是好事情,年轻人最初是尝试一下,到后来就成了一种坏习惯。十分奇怪的是,喝少量的酒会让我灰心丧气,而一旦大量饮酒,我的行动就如猛虎添翼。到了中年,我变得更加不能喝酒,但我并不劝告所有的人都去戒酒。其实喝水也可以达到与喝酒同样的效果。对于饮食,我还有一些可说的:一顿吃得多一些,要比吃得太少更容易消化。这是因为,要消化良好,就必须让整个胃都发挥作用,因此,一个人对于自己能吃多少,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在两顿饭之间不要喝咖啡,因为咖啡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情变得很糟糕。茶也只能早上喝,少喝一点,但要泡浓一些;如果茶水太淡,可能对身体有害,对心情也有不好的影响。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评判饮食的标准,不过总起来说,变化不会太大。如果天气让人不适,最好也不要喝茶,而去喝一杯可可,要浓一些,但应是去了油脂的。只要能够不坐,就尽量去活动;只有在户外自由活动中产生的思想才是值得信赖的,只有能鼓舞你的肌肉活动的思想才是值得信赖的。所有偏执行为可能都是产生于我们的内脏。我曾经说过,经常坐着不动,这是一种罪过。<br> 营养问题跟气候、居住地密切相关。一个要干大事情的人在这一方面很难有多大选择。气候对于身体机能活动影响极大,一个人如果在选择气候和居住地方面出现差错,可能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以至于抱憾终生。气候不适宜可能导致他缺乏足够的活力,无法获得一种欢快的自由,无法对自己说:只有我才能够完成这个。一旦内脏被麻痹,一个天才可能会变成庸人,变成德国式的人物。只有德国的气候才能使强健的内脏变得衰弱。随着身体机能活动的变化,一个人的精神也会跟着变得轻快或沉重;可以说,精神只是身体机能活动的一种形式。我可以列出许多大思想家住过或正在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大都气候干燥,他们住着十分安适自在。例如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等,这些地方的情况说明,天才人物必须依靠干燥晴朗的天气,也就是必须依靠身体机能的快速活动,依靠不断为自己获取大批能量的可能。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本来是很了不起的,智慧超群,但由于居住在气候不适宜的地方,变成一个眼光狭窄的专家和畸形变态人。如果不是疾病迫使我运用理性思考问题,我也会落到同样下场。长期在外行走,我已经有了很不错的观察气候的能力,从都灵到米兰这一段不长的路中,我都可以感受出空气湿度的变化。因此,想到一种情况我就感到后怕:直到最近10年,我都是在不适合自己的地方生活,其实我早就应该离开这些地方了。像瑙姆堡、普夫塔、胡利吉亚、莱比锡、巴塞尔、威尼斯等,都不适合于我的体质。如果说我对自己的早年生活没有留下什么愉快的印象,那并不是道德方面的原因,例如说我缺乏友谊;实际上直到今天我都缺乏友谊,但我并不感到不愉快。我生命中不幸的真正原因,是对于生理状况的无知;而这又是由所谓的理想主义造成的。由于这种理想主义,我一度迷失本性,去当一个语言学家,搞什么专门性的东西,而脱离了我本该从事的真正事业。没有任何一位医生或其他专家向我指出这一真正原因。在巴塞尔时,我花费的全部精力,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对我的非凡能力来说都是一种极大浪费。那时我缺乏一种敏锐的自傲,将所有的人都看得跟我一样,似乎处于无私状态,忘记了我与别人应有的距离,现在想起来很难原谅自己。只是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我才开始反省自己,发现这种理想主义之荒谬。正是由于疾病才让我走向理性。<br> ——《瞧这个人》<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