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卡巴拉:过去与现在
卡巴拉并非起源于当今好莱坞风格的噱头,这一点毫无秘密可言。实际上,卡巴拉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在卡巴拉出现时,人类要远比今天更加贴近自然。那时的人们与自然有种亲密无间的感觉,而且也积极地去培养同自然的密切关系。
在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多少理由去脱离自然。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疏远自己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其实,当时人类是自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主动加强同自然的紧密联系。
此外,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还不足以让自身感到安全;我们反而害怕自然力量——它们作为一种高于我们自身力量的超级力量,迫使我们接近自然。
人们之所以亲近自然,一方面是由于惧怕它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渴望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确定究竟是什么或谁在支配它。
早期的人类无法像今天那样避开自然因素的影响,我们在自己的“人造”世界里可以躲避自然的风雨侵袭,可早期的人类却无法这样去做。而最为重要的是,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及亲近自然的需求,许多人开始探寻并发现自然为他们,碰巧的是,为我们所有的人,所安排的规划。
探寻自然的那些先驱们想知道,自然是否确实有了目标,假如是这样,那么人类在这个总体规划中的角色可能是什么呢?那些掌握了最高层次的知识,即深入了解到自然的总体规划的人们,就是我们熟知的“卡巴拉学家”。
有一个人从那些先驱中脱颖而出,他就是亚伯拉罕。当他发现了自然描绘的总体规划时,不仅对它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第一次将它传授给别人。他认识到人类战胜恐惧、摆脱悲惨境况的唯一方法,就是全面了解自然为人类所准备的规划。而一旦亚伯拉罕意识到这一点,他便不遗余力地去教育渴望学习的人们。出于这种原因,亚伯拉罕作为第一位卡巴拉老师整个朝代的卡巴拉学家,而他手下最优秀的学生则成为下一代教授卡巴拉的老师,负责将从亚伯拉罕那儿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的学生。
卡巴拉学家将总体规划的设计者称为“创造者”,将规划本身称为“创造的念头”。也就是说,当卡巴拉学家谈论自然或自然规律时,他们是在谈论创造者,这一点相当重要。反之亦然,当卡巴拉学家谈论创造者时,他们也是在谈论自然或自然规律。这些术语是同义的。
卡巴拉学家(Mekubal)一词来源于希伯来单词Kabala(接受)。卡巴拉的原始语言是希伯来语,一门主要由卡巴拉学家发展并供自己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帮助他们就精神世界的事情相互沟通。后来出版的许多卡巴拉书籍,虽然用的是其他语言,但书中的基本术语一直沿用希伯来语。
对于卡巴拉学家来说,“创造者”这个词并不是指一种超自然的、与人类迥然不同的实体,而是指人类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知识时应该要达到的下一阶段。在希伯来语中,“创造者”的对应词语是Bore,它包含两个单词:Bo(来)和Re(看)。由此可见,“创造者”一词表示了“体验精神世界的私人邀请”的一种意思。
科学的摇篮
第一代卡巴拉学家获得的知识,远不止帮助他们认识到所有事物背后的规律。借助这些知识,他们能够解释我们碰到的自然现象。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老师,而且他们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成了古代与现代科学的基石。
或许在我们眼中,卡巴拉学家就是些躲在闪着昏暗烛光的密室中书写神秘经文的隐士。实际上,在20世纪末期之前,卡巴拉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接触卡巴拉的神秘途径,引发了围绕其本质的无数奇谈和传说。尽管大部分传说是错误的,但它们仍然能令甚至最缜密的思想家感到困惑。
戈特弗雷德?莱布尼茨(Gotfried Leibnitz,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微积分和数理逻辑的先驱,主要著作有《神正论》、《单子论》等),在谈及神秘现象如何影响卡巴拉时,就直言不讳地说道:“正是由于人们缺乏一把打开卡巴拉的神秘大门的钥匙,他们对卡巴拉知识的渴求,最终沦落为五花八门的流言飞语和迷信,进而产生了一种与真正的卡巴拉风马牛不相及的庸俗的卡巴拉,以及假借魔术的名义杜撰的各种各样的幻想,而且当时许多书籍中讲述的就是这些内容。”
然而,卡巴拉并非总是神秘的。其实,第一代卡巴拉学家从不将自己学到的知识据为己有,他们从不深居简出,故步自封,而是积极投身社会,传播知识。很多时候,卡巴拉学家都在各自的国家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位。在所有这些领导者中,大卫王或许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既是伟大的卡巴拉学家,又是伟大的领导者。
卡巴拉学家积极参与社会,这极大地帮助了当代学者奠定我们如今了解到的“西方哲学”的基石——后来演变为现代科学的基石。在这方面,约翰尼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德国人文主义者、古典学者,古代语言及传统的专家)在其著作《卡巴拉的艺术》中写到:“我的老师,哲学之父毕达哥拉斯,从卡巴拉学家那儿结出了他的教义……在毕达哥拉斯那个时代,人们尚不知道“卡巴拉”这个词语,他是第一位将该词翻译为希腊语“哲学”的人……卡巴拉没有让我们生活在俗世之中,而是将我们的思维提升到知识的高度。”
其他路径
然而,我们不能将哲学家与卡巴拉学家混为一谈。这是因为许多哲学家并没有研究过卡巴拉,所以无法透彻掌握卡巴拉科学的深层知识。这样一来,本该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去发展和对待的知识,则被错误地发展和对待了。倘若卡巴拉知识传播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而当地当时碰巧没有卡巴拉学家,那么它便会走上一条不同的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便绕道而行。尽管西方哲学包括了卡巴拉知识的部分内容,但它最终却选择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西方哲学衍生了研究我们物质世界——我们靠自己的五种官能感知的世界的科学。但卡巴拉却是一门研究我们感官感知范围之外所发生的事情的科学。这个侧重点的改变,使得人类与卡巴拉学家们获得的原始知识背道而驰。这种前进方向的变化,令人类绕路,而由此引发的后果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探讨。
重大问题
大约2000年前,卡巴拉变成了秘而不宣的科学。原因非常简单:当时它没有社会需求。从那时起,人类忙于发展一神论宗教,稍后又将发展重点转移到科学上。宗教与科学之所以被创立,是因为人类需要用它来回答自身碰到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为何来到世间?”
时至今日,许多人空前感到2000年来一直在起作用的东西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了。宗教与科学提供的答案已不再令他们感到满意。针对有关人生目标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人开始向别处寻求答案。他们转向了东方教义、占卜、巫术和神秘主义,而有些人则转向卡巴拉。
由于卡巴拉正是为回答这些基本问题而创立的,因此它提供的答案与其息息相关。借助重新发展有关人生意义的古老答案,我们实际上在修补着当初由于疏远卡巴拉、亲近哲学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痕。
卡巴拉的诞生
大约5000年前,卡巴拉在位于今天伊拉克的一个古老的国度美索不达米亚“初登舞台”。美索不达米亚不仅是卡巴拉的诞生地,还是所有古老教义和神秘主义的诞生地。在那里,人们信奉多种不同的教义,而且经常同时遵循了好几种教义。占星术(以观察天象来预卜人间事物的一种方术)、算命、数字命理学(根据出生日期等数字来解释人的性格或占卜祸福的)、魔法、巫术、符咒、恶毒眼光(一种迷信说法,此种眼光可使人倒霉或遭受伤害)——所有这些都在素有古代文化中心之称的美索不达米亚得以发展、兴盛。
只要人们对自己的信仰感到满意,就不会有改变信仰的需求。人们想知道什么会让他们的生活平平安安,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方可过得舒适惬意。他们大都不会去询问人生的起源,也不会去探求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谁或是什么创立了生活的法则。
粗略一看,这二者之间似乎只有很微小的差异。实际上,询问有关人生的问题,同探求塑造人生的法则之间的差异,就像学会驾驶一辆汽车与学会制造一辆小车之间的差异。它完全是不同层次的知识。
变化的动力
愿望不会从天而降。它们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于我们内心,而且只有当它们变为某些可以阐述的东西,比如“我想吃一张比萨饼”……的时候,它们才浮出来。在此之前,我们要么感觉不到愿望,要么至多感到通常的那种不安。我们都体验过那种渴望某件东西的感觉,但却并不十分清楚它是什么。好了,它就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愿望。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过:“需要是发明之母”。他这句话很正确。同样,卡巴拉也教我们认识到,我们能够学会任何技能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要想去学习它。这是个很简单的公式:当我们想要某件东西时,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得到它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挤出时间,积聚能量,培养必要的技能。事实证明变化的动力就是愿望。
我们内心愿望的演变方式,既阐释又设计着整个人类历史。随着人类愿望的发展,它们促使人们研究其所处的环境,以便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与矿物、植物和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在一刻不停地进化着。每一代、每一个人的愿望都在变得愈加强烈。
坐上驾驶位
变化的动机——愿望——可以被分为从0~4共五个层次。卡巴拉将这种动机称为“一种接受满足的意愿”,或者简单称其为“接受的意愿”。当卡巴拉在5000年前第一次出现时,“接受的意愿”处于0的层次。时至今日,你可能已经猜到,我们的“接受的意愿”处于4的层次——最强烈的愿望层次。
然而,在早些时候,当“接受的意愿”处于0的层次时,愿望由于不够强烈,因此无法将我们同自然分离,将我们彼此分离。在那个时候,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今天我们许多人花大把大把的钱在冥想课堂上重新学习它(让我们敢于面对它,尽管结局并不总是成功的)——则是生活的自然方式。人们并不知道任何其他方式。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能脱离自然,更不用说他们内心产生那样的愿望了。
实际上,在那些日子里,人类与自然的沟通及人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是那样的通畅,以至于语言不再成为必需;相反,人们靠思想沟通,非常类似心灵感应。那是一个团结的时代,整个人类就像是一个民族。
然而,仍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文明的发源地、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愿望日渐强烈,他们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人们开始想改变自然并为己所用。他们不再想让自己适应自然,而是开始想要改变自然,让其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与自然相分离,愈加疏远自然,疏远自己的同胞。今天,时间已经过了许多个世纪,我们却再次发现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是行不通的。
当然,当人们开始将他们自己置于环境和社会的对立面时,他们不再将他人看成亲人,也不再将自然当作家园。仇恨取代了关爱,人们彼此间愈加疏远。
这样一来,古时的同一个民族被分裂了。它首先分裂为两大集团,一个向西发展,一个向东扩张。这两大集团继续分裂,最终形成我们今天的众多国家。
这种分裂的最明显的症状——被《圣经》描述为“巴别塔的倒塌”——就是不同语言的产生。这些不同的语言将人们彼此分离,并制造出困惑和障碍,引起了混淆、杂乱的状态。困惑的希伯来文为Bilbul,为了表明人们内心的困惑,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取名为Babel(巴比伦)。
自从产生了分离——当我们的愿望从0层次提升到1层次时——我们与自然之间出现了对抗。然而,我们并没有去改正日渐滋长的自我主义,从而让自己与自然融合,也就是说,让自己与创造者融合;我们反倒去制造一道机械的、技术的屏障,将我们与自然隔离开来。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初衷,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存脱离自然因素的影响。可结果表明,我们实际上(无论是否意识到)是在企图控制创造者并坐上驾驶位置上。
当这种困惑产生的时候,亚伯拉罕还生活在巴比伦,帮助父亲制作一些小偶像,并在自家的商店里出售。由此不难看出,在素有古代纽约之称的巴比伦,各种思想鱼目混杂,生活在那儿的亚伯拉罕对此有切身的体验。这种困惑也解释了亚伯拉罕为何要执著地求索,并在后来发现了自然规律:“谁是在控制着这一切?”当他认识到这种困惑与分离是有其目标的,他很快将自己的心得传授给愿意倾听的人们。
隐匿、寻找却毫无发现
人类自私自利的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升,可每提升一个层次,我们就离自然(创造者)越远。在卡巴拉中,距离不是用公里或米来测算的;它是用品质来测算的,创造者的品质是完美的、团结的和给予的品质,只有当我们具备了它的品质,我们才能够感觉到它。如果你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么你根本无法与利他的和完整的创造者连接。这就像我们试图看清与自己背靠背站着的另外一个人一样。
正是由于我们与创造者背靠背站立,而且由于我们仍想控制它,所以我们越是极力那样做,越会有种受挫感。当然,我们无法控制某些我们看不到的甚至感觉不到的事物。这种愿望永远不可能实现,除非我们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从相反的方向去察看,才能够发现创造者。
许多人已经厌烦那些技术未兑现的要给我们带来财富、健康和未来安全的承诺。今天,能获得所有这一切的人寥寥无几,而且甚至连他们也无法肯定到了明天自己依然还能不能拥有这一切。但这样一种状态的好处,就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检查我们的前进方向,并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一直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呢?”
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正面临着危机和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我们不应该再通过选择技术来让自己脱离自然,从而实现利己主义;而应该将我们的利己主义转变为利他主义,从而与自然合一。
在卡巴拉中,用来表述这种转变的术语为Tikun (改正)。要想认识到我们与创造者相互对立,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5000年前发生在我们(人类)之间的分裂。这种过程被称为“感知到邪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它是迈向真正健康和幸福的第一步。
全球危机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从美索不达米亚分裂出来的两大集团在过去的5000年里,分别演变成了由很多不同的民族构成的文明。在这两个原始的集团中,一个变成我们所称的“西方文明”,而另一个则成了所谓的“东方文明”。
这两大文明之间的矛盾在第一次分裂时就开始出现,而如今日益恶化的冲突则反映出这种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极致。5000年前,一个单一的民族因为利己主义的滋长而分裂,这个国家的民众之间也出现了裂痕。现在到了这个“民族”……人类——重新统一,再次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的时候了。我们仍然处于那些年前所出现的断裂点上,只是如今我们更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依照卡巴拉智慧,这种文化冲突及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盛极一时的神秘信仰重新抬头,标志着人类要重新团结为一种新文明。今天,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必须找回分裂之前所处的那种状态。借助重建一个团结的人类社会,我们还将重新确立与自然的联系,与创造者的联系。
利己主义是一种僵局
在神秘主义流行期间,卡巴拉的智慧被开发出来,它让人们了解到有关利己主义逐步滋长的知识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卡巴拉学家教育我们,宇宙间存在的万事万物都由渴求满足自己的愿望所造就。
然而,如果愿望是自私的,那么就无法以其自然形式被实现。这是因为当我们满足一种愿望时,我们就消除了它;而如果我们消除了对某件事物的愿望,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再从这件事物中得到乐趣。
比如,你不妨考虑一下自己最喜爱的食物。现在想象着你自己来到一个美妙的餐厅,舒适地坐在餐桌前,这时一位满脸笑容的服务员给为你端来一盘盖着盖子的佳肴,并将它放在你的面前,随后将盘上的盖子拿掉。啊!那么熟悉的美味!你自己还没有享受吧?可你的身体已经开始享用它了!你在头脑中想象着美味佳肴时,你的体内就开始分泌胃液了。
然而,就在你开始吃的那一刻,这种快乐就减弱了。你吃得越饱,你从吃中得到的快乐就越少。最终,当你酒足饭饱时,你就无法再享用食物了,于是你停止进餐。你之所以不再吃了,不是因为你一点也吃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你吃饱之后,吃对你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你这就是陷入了利己主义的僵局——如果你拥有了自己所渴望的东西,那么你就不再想要它了。
由此可见,由于我们没有了快乐就无法生活,因而我们必须去继续寻求新、更大的快乐。我们靠培养新的愿望来做到这一点,而这些新的愿望同样也不会得到完全满足。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很明显,我们想要得到越多,我们就感到越空虚。我们越感到空虚,就越感到迷惑不解。
而且由于我们的愿望目前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层次上,我们便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乏满足感,即使我们明显比我们的祖祖辈辈拥有的物质财富更多。一方面,我们拥有很多;另一方面,我们日益不满。这两者间的对比,正是我们如今所经历的危机的实质所在。我们变得越自私自利,我们就越感到空虚,而它引发的危机则会越发严重。
利他主义的必要性
最初,所有的人都是相互连接的。我们感觉到并认为自己是具有同一性的人类,而自然也正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这种“集体的”人类,被称为“亚当(Adam)”,源于希伯来文的Dome(相似的),意味着与创造者相似,创造者也是统一的、完整的。然而,尽管人类当初是同一的,但随着我们利己主义的滋生,我们渐渐丧失了团结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了。
卡巴拉著作中写道,自然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的利己主义不断滋长,直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已经疏远,甚至互相憎恨。这个计划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感觉到人类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随后受自私自利的影响而分裂为一个个相互疏远的人们。只有到了那里,我们方才意识到我们与创造者背道而驰,我们成了十足的自私之人。
此外,这是我们意识到利己主义是消极、无法满足、毫无希望之物的唯一途径。正如我们前面所讲,我们的利己心将我们彼此分离,将我们与自然分离。而为了改变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这样做能够促使我们渴望变革,靠着自身的努力去寻求一条将自己转变为利他主义者的道路,重新建立与全人类的联系,与自然——创造者——的联系。我们毕竟已经说过愿望是变化的动机。
卡巴拉学家耶胡达?阿斯拉格写道,最高之光进入和离开愿望的过程,让容器(愿望)变得适合完成其使命——利他的生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感到与创造者的团结,那么我们必须首先与其连接,随后去体验这种连接的丧失。在体验过这两种状态之后,我们将能做出有意识的抉择,而这种意识是真正团结的必需。
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比作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真实体验:当他还是一个婴儿时,他感到与自己的父母密不可分;当他成长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具有一种反叛精神;而最终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时,便懂得并辩解自己的父母。
实际上,利他主义并不是一种选择。表面看来,好像我们能够在“是做一个自私自利之人,还是做一个利他之人”之间进行选择。然而,如果我们检验一下自然,就会发现利他主义是最根本的自然规律。例如,身体中的每个细胞固有是自私的。但为了生存,它必须为整个身体的健康着想,从而别无选择地摈弃它的自私倾向。这个细胞为此得到的回报,就是它不仅体验到它自身的存在,而且体验到整个身体的勃勃生机。
我们相互之间也必须培养一种相似的关系。随后,我们彼此结合得越成功,我们就越能够感到亚当的永恒存在,而不是感觉到我们并不长久的物质存在。
尤其在今天,利他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根本。我们大家都密切相连,相互依靠,这一点不言而喻。这种依靠对利他主义作出了一种全新的非常准确的定义:任何一种行为或意图,只要源于将人类融入一个同一体的需求,都可被视为利他。反之,任何一种行为或意图,只要它不关注人类的团结,就是利己。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一切痛苦悲伤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背离自然。自然界的其他一切——矿物、植物及动物——都本能地遵循着自然的利他法则,只有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界的矿物、植物及动物的行为相反,与创造者的行为相反。
此外,我们看到自己周围的那些悲伤与痛苦,并不只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自然界的所有其他部分也都会因为我们的错误行为而遭殃。如果自然界的每个部分都本能地遵从自然法则,而且如果只有人类不去遵守自然法则,那么人类就成了大自然中唯一的破坏因素。倘若我们能够改正自己,即从利己主义转变到利他主义,那么其他一切自然部分也会得到改正,这个世界的生态恶化、饥荒、战争和其他社会问题也会得以解决。
增强的感知
利他主义能给我们带来特别的回报,我们从利己转变为利他,似乎只是做出了将别人的利益放在我们自己前边这样一个改变,可它实际上却能让我们受益。当我们开始考虑别人时,我们便整合于他们,而他们也整合于我们。
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它:今天全世界生活着大约70亿人。假如你不是靠着自己的两只手、两条腿和一个大脑去统治全人类,而是让140亿只手、140亿条腿和70亿个大脑去统治全人类,情况又该如何呢?这话听起来让人有点困惑吗?实际上不会的。这是因为所有那些头脑都会像一个单一的头脑一样操作,那么多只手也都会像一双手一样工作。全人类就像一个躯体那样发挥作用,这具躯体的能力将被提升70亿倍。
且慢,我们得到的回报还不止这些,任何一个坚持利他主义的人除了成为超人之外,还会收到所有人最梦寐以求的礼物:全知,或者完全记起与完全了解。由于利他是创造者的本质,因此获得了它就意味着我们也具备了创造者的本质,我们开始像它那样去思想。我们开始知道一切事情为何会发生,应该何时发生,而且如果我们想让它产生不同的结果的话,应该做些什么。在卡巴拉中,这种状态被称为“形式同等”,而且这正是创造的目标。
这种提升了的感知状态,这种形式同等的状态,解释了当初我们为何要被创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最初我们以统一体被创造的,而随后经过破碎——以便我们能够重新团结。在这种团结的过程中,我们将懂得自然为何以它那种方式行事,而且会变得像创造自然的思想那样明智。
当我们与自然结合时,我们就会感到像自然那样永恒和完美。在那样的一种状态中,即便我们的肉体死亡了,我们仍将感觉到自己继续存在于永恒的自然中,物质层次上的生与死不再对我们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以前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知将被一种全面的利他的感知所取代,我们自己的生命将变为整个自然的生命。
时机就在现在
素有卡巴拉的《圣经》之称的《光辉之书》,是在大约2000年之前撰写的。它声称到20世纪末期,人类的自私自利将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想得到的越多,我们就越感到空虚。鉴于此,自20世纪末期以来,人类一直在经历着最为严重的空虚。《光辉之书》还写到,当感到这种空虚时,人类将需要一种治愈它的手段,借助这种手段让自己获得满足感,随后《光辉之书》告诉我们,将卡巴拉作为一种通过与自然通话来获得满足的手段,介绍给全人类的时机终将到来。
获得满足的过程,也就是希伯来语中所说的Tikun(改正),不会立即完结,而且每个人也不可能不同步完成这一过程。如果它要发生的话,那么人们就必须首先想让它发生。它是一个从人们自己的意志中演变出来的过程。
当人们感知到他或她的自私的本质是一切邪恶的根源的时候,改正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强烈的体验,而它总是让人想去变革,想从利己转变为利他。
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创造者把我们作为一个单一的团结的创造物来对待。我们曾自私地企图实现我们的目标,可如今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只有靠集体的努力和利他主义才能得以解决。我们越多地意识到我们的自私自利,我们就越渴望利用卡巴拉的方法来将我们的本质转变为利他。当卡巴拉刚刚出现时,我们并没有这么做,但现在我们能这么做了,因为现在我们认识到自己需要它!
过去5000年的人类进化就是尝试一种方法的过程,在其中我们检验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快乐,对其感到失望,摒弃并去寻求另外一种方法。我们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却并没有一个能让我们感到更加幸福。
既然卡巴拉手段(其目标是最高层次的利己主义的改正)已经出现了,我们就不必再踏上幻灭的道路。我们只借助卡巴拉改正我们最严重的利己主义,其他问题也便迎刃而解,于是在这个改正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满足、灵感与欢乐。
卡巴拉的智慧(接受的智慧)最早出现在大约5000年前,当时人类开始探讨他们存在的目的。那些了解了它的人们被称为“卡巴拉学家”,他们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知道人类在宇宙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但在那些日子里,大多数人的愿望太小,以至于未能努力寻求卡巴拉知识。因此,当卡巴拉学家看到人们并不需要这个智慧,他们便将它隐藏起来,并在暗中等待着大家都乐意接受它的那个时刻的到来。与此同时,人类开辟了诸如宗教与科学的渠道。
时至今日,当越来越多的人深信宗教与科学并不能解答人生最深层次的问题,他们便开始从别处寻求答案,这就到了卡巴拉一直在等待的那个时刻,这就是为何卡巴拉会重新兴起——为了解答人类存在的目的。
卡巴拉告诉我们,自然——创造者的同义词——是完整的、利他的、团结的。它还告诉我们,不要只懂得自然,我们还必须有一个亲自实践某种存在方式的愿望。
卡巴拉还对我们说,这样做我们不仅能与自然同化,而且还会懂得自然思想背后的总体规划。卡巴拉最后声称,靠着了解总体规划,我们将等同于总体规划的描绘者,而这就是创造的目标——人类变得与创造者相同。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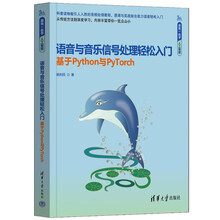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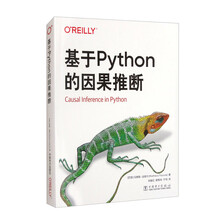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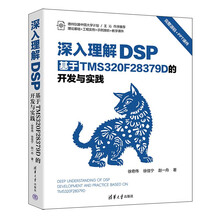
——Jeffrey Satinover博士(法国尼斯大学物理系教授)
迈克尔·莱特曼是独特而令人着迷的:一位创造出了一个科学与卡巴拉富有意义的综合体的天才科学家。
——David A. Cooper(《狂喜卡巴拉》的作者)
对于那些寻找可信的传统神秘犹太教导的人们而言,这是一个极好的资源,一个严肃的学生们已遵从了数百年的方法。
——Arthur Goldwag, 《对卡巴拉的信念之网指南》
这儿没有系着红线的秘方,没有唾手可得手的对世俗成功的许诺。相反,莱特曼邀请我们通过挑战,即通常是痛苦内心的工作,来对自我及这个世界进行改造。令人着迷的,富有学识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这些将唤醒并激励任何一位精神真理的探求者。
——Tamar Frankiel博士(《卡巴拉的礼物》作者)
在此决定我们在这个星球未来的危急时刻,卡巴拉这一古老智慧已经复兴并成为中肯和有效的方法。在这一古典手稿中所包含的智慧必须被拿出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抓住对我们开放的机会。 在全世界对我们所有人要传达这一讯息。迈克尔?莱特曼正是能够迎接这一重要挑战并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合格人选。
——拉斯扎罗(Ervin Laszlo)教授(系统哲学和进化综合理论领域的权威)
卡巴拉科学给予我们一个通往精神世界和我们存在之根源的实用方法。人存在于世上时,如果能实现生命的真正目标,就能获得完美、和谐的生活及无限的满足感,并超越此世界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迈克尔·莱特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