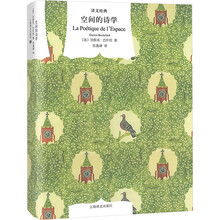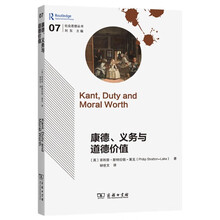或者说作品自身中隐含的一种尚未实现的意义和真理的指令。伽达默尔以乐曲为例:乐曲的乐谱实际上就是一种指令,它包含着乐曲的种种可能性;但是,听音乐不是读乐谱,只有不同的境遇中演出才能够把乐曲中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得以表达和表现出来,乐曲本身就是那在演出事件中所发生的东西,它“为了存在而期待境遇,并且通过其所遇到的境遇才规定了自身”④。正是由于艺术作品不断随着境遇的变迁而重新规定自身,偶缘性才构成了艺术作品存在本身的本质要素。但这也就意味着,艺术作品的存在及其真理本身就具有一种不确定性与开放性,以偶缘性或者说诠释学境遇为其本质要素的作品的意义总是“比没有这种境遇要包含更多的东西”。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一部艺术作品是如此紧密地与它所关联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致这部艺术作品如同通过一个新的存在事件而丰富了其所关联的东西的存在。”②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前文已经探讨过的作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探究的存在论结论的“存在的扩充”。
由此,我们可以在艺术真理问题上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一方面,从偶缘性即是作品存在的诠释学境遇来看,艺术作品的真理也必须是诠释学境遇之中的真理。另一方面,从偶缘性构成作品存在的本质要素来看,艺术真理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理解的事件:在存在论上,艺术真理表现为存在的扩充与意义的敞开;在诠释学上,艺术真理表现为意义的发生与理解的增殖。这表明艺术的真理就是理解的真理,也就是诠释学的真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