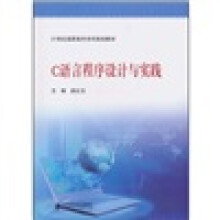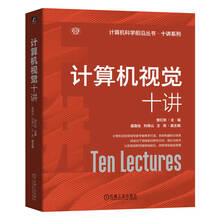对于七子与唐宋派的并不“异趋”,艾南英做出更为明确的阐发,其《答陈人中论文书》云:“夫韩、欧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汉之舟楫也。”(《天佣子集》卷三)“舟楫”之喻,与茅坤以唐宋八家为“操觚者之券”取譬不同而取义相似,更进一步,如果说前后七子为了救八股之弊而上溯六艺,但六艺已远须取径秦汉,那么在艾南英及其所亲近的唐宋派看来,并秦汉亦已久远而须取径唐宋名家一一以唐宋韩欧之文为“舟楫”,至于秦汉而再溯六艺。通过如此“舟楫”摆渡的接力,不同文学时代之间相互衔接起来。换句话说,秦汉文章与唐宋文章,原本因为一些偏激的文学主张而不免关系紧张,但最终互通“舟楫”,趋于一致。由正题而反题而达到合题,逭也正是易于为一般文学现象所掩盖的文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由明而清,仍然“舟楫”可渡。桐城文派之祖方苞《古文约选序例》云:“是编所录,惟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耳。”而经由八家“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易“舟楫”为“津梁”,恰如清廷之延续有明八股取士,方苞也把七子和唐宋派的主张打成一片继承下来。姚鼐门人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云:“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序也,学者必先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漠,亦茫无津涯。”(《刘孟涂文集》卷四)可见循八家之法,窥秦汉“津涯”,盖已成为桐城派内家法,一脉以承。与方苞差不多同时的唐彪作《读书作文谱》,以为古来佳文虽多,“至于永叔、子瞻之文,初学尤宜先读,以为造就之阶,则工夫易于人手。”“自归震川、钱牧斋二先生读欧文,且极口称赞,自此诸名公皆争效法,而欧文遂为古学津梁矣。”可见对八家古文“津梁”之认识,盖已越出桐城派外,成为风气。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