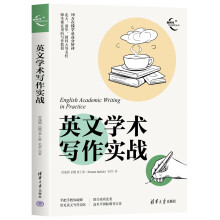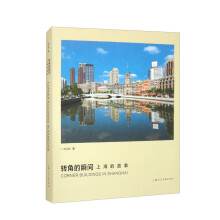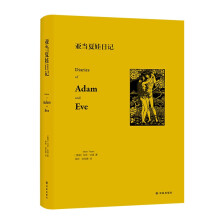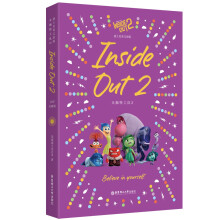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此四子者,各于其不同之时代及环境中,发为不朽之歌声。然荷马史诗中之英雄,既与吾人之现实生活相去太远;但丁之天堂地狱,又与近代思想诸多低语;歌德距吾人较近,实为近代精神之卓越的代表。但以超脱对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其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不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
中国读者耳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曾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然无存,甚至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阅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余笃嗜莎剧,曾首尾研涌全集至少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开四年春,得前辈同事詹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越年战事发生,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译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全数毁于炮火,仓卒中只携出牛津版全集一册,及译稿数本而已,而后辗转流徙,为生活而奔波,更无暇晷,以续未竟之志。及卅一年春,目观世变日亟,闭户家居,摈绝外务,始得惠心一志,致力译事。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三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是否顺口,音节是否调和。一字一字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然才力所限,未能尽符理想;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谬误之处,自知不免。所望海内学人,惠予纠正,幸甚幸甚!
原文全集在编次方面,不甚惬当,兹特依据各剧性质,分为“喜剧”、“悲剧”、“传奇剧”、“史剧”四辑,每辑各自成一系统。读者循是以求,不难获见莎翁作品之全貌。昔卡莱尔尝云:“吾人宁失百印度,不愿失一莎士比亚”。夫莎士比亚为世界的诗人,固非一国所可独占;倘若此集之出版,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则译者之劳力,庶几不为虚掷矣。知我罪我,惟在读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