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喜欢和自己的子女做朋友,因此孩子们在家里可以享受到平等的地位,也拥有很多权利。比如说,他们有隐私权,家长没有经过同意是不能随便进入孩子的房间,不能随意翻阅其信件和日记的。家里有大事发生时可能会召开家庭会议,每一个家庭成员在会上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即使是幼子的观点,只要是好的也会被采纳。当然,给孩子自由是有利有弊的,它可以使家庭更加和谐,但过分放纵也会酿成恶果。而有一些中国家长对子女的过分束缚同样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因此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一定要把握住一个“度”,在一个恰到好处的自由度下成长的孩子在将来才能有最健康的发展。
做为孩子的朋友,美国的一些父母会特意抽出时间与他们共度特別的时光。一起去公园玩耍,一起在临睡前读本好书(大人读给孩子),一起做一件小小的“艺术品”,在孩子幼小的时候;一起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游,一起看一场轻松的电影,一起去吃顿美味的菜肴,在孩子成长的时候;一起促膝长谈,一起探讨人生,一起倾吐心声,在孩子成熟的时候。这对于双方都会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它可以帮助人们互相了解,共同努力跨越那条时代造成的鸿沟,建立起凌架于骨肉亲情之上的特殊友谊。
每当一个学期将要结束时,学生们都会喜忧掺半。喜当然是因为盼望已久的假期就在眼前;忧则是因为放假前还有一关要过——成绩单。对于中国孩子来说,一份不好的成绩单会使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会使他的整个假期黯然无光。然而在美国,每个学生年终的成绩单都是一件私人的物品。同学之间通常是不会知道彼此的分数的。家长方面也不会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得到A或B可能要给与鼓励;而得到D或F(F表示不及格)就需要一些激励。分数在大人心目中的重要程度比能力要差得远,所以很少会有家长因为子女没有考到班内前10名而大发雷霆。当然,他们也没有条件这样做,因为美国的学校是不公布成绩名次的。对于那些学习极其出色的学生会有其他形式的奖励,比如像Honor ROll(直译即光荣榜)就是其中一种。对于差生学校则可能给予一些特别的帮助。那里的主旨是“尽全力”,可中国大部分学校的主旨是“得高分”。
在美国读书时我尽全力得到了高分。当时我的数学成绩特别好。六年级之前我曾经接受过一次测试,结果发现我的数学在解题方面已经达到十一年级水平,于是进入六年级后我便得到学校批准在七年级上数学课。离开那所学校之前我还得到了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数学少年班“进修”的机会,但因为快要回国了所以没有去。回到中国之后,我的英语远远超过了中学学习的水平,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大学旁听英文课,可谁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给我继续学习英语的机会,相反我却得到了学校的特别许可免修了英文课,所以我有时会开玩笑说自己一直顽固地保持着美国小学六年级的英语水平。当然,我也会寻找一些其他的渠道去在这方面不断地“充电”,然而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两个国家在学习机会的给予方面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另外,美国的大部分学校都有一个为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儿童所开设的课程(清注意所谓“特殊才能”并非指身体方面的特异功能,而是智商方面的)。这种课通常都是在课余时间由特殊老师专门辅导,目的是使孩子们的才能和潜力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开发。我曾经上过数学和写作方面的课。数学课上只有我和老师两个人,我们在一起做的那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数学这个领域里出现的。她教我用数学方法画出各种奇异的图形,给我出了无数道逻辑问题,帮我攻破许许多多“脑筋急转弯”。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接触的第一道题。问:一个大印第安人和一个小印第安人一起去打猎,小印第安人是大印第安人的儿子,而大印第安人却不是小印第安人的爸爸。这是怎么回事?想好了吗?答:她是他的妈妈。在写作班上我们自己写儿歌歌词。美国有一些流传很广的儿歌,它们对人们的影响很大,甚至会伴随其一生。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玛丽有只小羊羔”以及一个名叫Dumpty的蛋壳人的故事等等。我改写的一段歌词是:“玛丽有只小羊羔,其毛白似棉花。不幸羊羔被烧烤,再也见不到它,”好像有点儿太残忍了,给那只可爱的小羊羔一个如此凄惨的结果,不过老师说我有想像力。这一点我不客气地承认了,因为有时我的思想确实很疯狂。
回到了旅店,已经饥肠辘辘的我自告奋勇地去准备午餐。如果不是饿成那样儿,企图“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如此积极的。我倒好了牛奶和橙汁,切好了面包和香肠,正迫不及待地要“先吃为快”时,突然发现香肠的断面处隐约可见一些白色的固体。不像是油,更像是……碎骨头。深感奇怪的我把它拿给妈妈“鉴定”。包装上印着一张图片,主角是一只白色的小猫,那种典型的应该叫做“雪球”的小白猫。她真漂亮,与屋里电视屏幕上的小猫一样漂亮。不对,电视上的那只猫根本就是她嘛。电视机虽然是开着的,但是我们谁都没有在看。以我们那可怜的“你好,再见”级的法语水平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开着它只是为了可以体会一下法国电视节目的感觉。而这只猫的出现却一下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可越看感觉越不对。那只猫正在吃香肠!
终于真相大白了。“这是猫食!!!我的天哪,真要命。”我带着几分侥幸说道。谢天谢地我们谁也不曾“勇敢”地去尝试一番。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有意或无意地(最好是后者,否则他就有问题了)把猫食与人食放到了一起,我们这几个不识法文的人便稀里糊涂地把它买去—了,幸好没有再稀里糊涂地把它吃下去。不知道假如稀里糊涂吃了会有什么后果——会长猫耳朵吗?
三天之后,我们离开了巴黎,继续法国的“浪漫之旅”。接下去的目的地是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瓦尔第塞尔,我们要在那里停留半个月。这将是非常舒适的一段日子,因为这里的轻松与随后十五天里的:忙碌相比简直是一种奢侈。我们会在后半个月内马不停蹄地跑遍欧洲大陆上的将近三十个城市。因此这个著名的滑雪胜地不仅是父亲开会的地方,也是我们养精蓄锐的所在了。小镇位于山上大约海拔1800米处。我们乘坐的车子缓缓地在蜿蜒的公路上向上爬着,我却发现耳朵的感觉不对劲了。我的双耳对于高度的反应极其灵敏,每次坐飞机或是坐电梯到很高的地方时都会有异样的感觉。这一次真麻烦,到达目的地时我差不多已经部分失聪了。于是我便真真正正地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假期,一切都是半音量的。
除了让我听不清楚之外,对于瓦尔第塞尔我还是十分满意的。那是一座恬静典雅的小镇,其中大部分人口都是四季络绎不绝的游客。会议在当地惟一一家四星级酒店召开。我很高兴地发现自己并不孤独,因为周围有许多随父母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龄人。更令人高兴的是,大家都会讲英语,交流起来没有任何障碍。大人们研会的那些日子全部被不同肤色融合而成的快乐占据了。
而爬山终究是大事。每一个来到阿尔卑斯山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去征服它。我要爬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一直不相信山上会有雪。眼见才为实嘛。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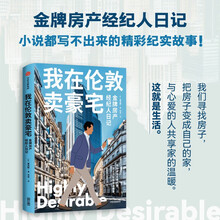



即使在我们成人,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自己曾在八十年代中期留学美国,正是书中所写的那一段日子。多少昨天故事和情绪记忆,正欲忘去,忽然读到此书,又被一一勾起,好像旧友重逢,让我不时掩卷长思。我与这本书的作者查可欣小友素昧平生,却竞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通过这本书,我仿佛曾与她深交长谈,仿佛进入了她的世界,为她在美国的辛酸喜乐动情不已。因为那也曾是我的辛酸喜乐,而我却没能像查可欣那样,真实准确而又带着孩童情趣把它们写下来。
国內近年来由我们这些“大人”写成的反映留学生活的作品日见其多,但多数与“小留学生”查可欣的这部作品一比,顿时显得如此苍白幼稚令人汗颜,不是英文没有过关,就是肤浅到观光游记的水平,更有的作品根本就是在瞎编。完全没有进入美国社会,更谈不到了解西方文化。再看看这部书!全书英汉对照,其英语部分文通字畅,口语道地,非“童子功”是达不到的。而汉语部分又绝非单纯直译,看得出重新写过的匠心。最难得的,还是这本书的真实,不加修饰的真实,以孩子的奇特经历、敏锐观察和独到眼光所构成的真实,我们这些成人作者是无论如何模仿不来,比拟不了的。
我的职业要求我是一个“星探”,我的天赋使我对有特殊才能的人有着特殊的嗅觉——即使在他们尚默默无闻的时候。当然,更有着一份特殊的敬意。
亲爱的读者朋友,请相信我的话:查可欣是这些奇才中的一个。我相信这个女孩的能量和才华不仅于这本小书。我期待在未来更多地看到和听到查可欣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