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总结
不存在知情权。
在宪法中找不到知情权。宪法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机构权利。更确切地说,知情权是法庭的发明,所以只是一种可以随时拿走的特权。在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以前,必须对知情权有比现在更多的认可。“信息自由运动”原本主要是为了取得接近政府资料的合法权,但现今已经扩大了目标,要求包括得到一个普遍的知情权。然而现在,就算只是接近官方资料的权利也严重地受到了各种例外情况的限制。比如隐私、经济利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回 应
梅里尔:存在知情权。
我的合作者认为知情权不是宪法所保障的一项不可分割的权利,而是由仁慈的立法机构给予的或是由新闻记者发明创造的东西。要对其中的任何观点加以争论都很困难。这种权利并没有在《权利法案》中公开地写明。而且似乎只有记者和公众利益的倡导者才会费力去解释这项权利。
话虽如此,我却仍然坚持认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自由和开放)的公民来说,知情权的确存在——就算这种权利还只是在理论阶段,尚未实在地写入《第一修正案)。在我看来,不管目前宪法中是否有这样的条款,根本的或自然形成的权利都存在着,这种权利在适当的时候就会成型。我相信“知情权”最终会出现并获得合法地位,尽管目前政府(在这里或世界上其他地方)暂不承认它是一项真正的权利。
人民的知情权没有明确地写入宪法,或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记者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发明这种权利,他们从新闻自由条款推断出人民知情权的存在。我猜想他们做出这个在我看来非常合理的推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算是发明了知情权。记者们已经看到这项公共权利站在支持新闻法律自由的哲学阴影之下。
如果他们心存内疚的话,他们应为此感到骄傲,而不是内疚。
我们应该问一问为什么美国的缔造者们要制定《新闻自由法》。难道只是为了拥有一个自由的媒体本身吗?只是为了后人夸耀这样一个条款?很明显,《权利法案》中之所以有新闻自由(还有言论自由)条款,概因有一个实用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民的知情权相关。假如共和国的统治者(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了解公众事务和政府事务,他们当然不能成为好的统治者,也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他们必须知道自己在怎样的哲学框架中。他们的政府建立在他们会知道的假设上。所以,这是他们的知情权。他们需要了解。为了和自己的政治目标相符,他们就必须从理论上得到授权。同样,为了实现新闻自由,就得有知情权。
有人会问:如果人民有知情权,那么媒体和政府是不是有责任帮助他们了解情况,获得信息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媒体要求这项权利(我坚持自由社会中享有新闻自由的媒体必须坚信这项基本权利的存在),那么他们必须认真地担负起为人们提供有关公众事务的消息的责任。假如存在知情权(我相信是有的)。那媒体就担负着实现这项权利的重大责任——保证人民能够了解情况。
在这一点上,必须提到政府。因为媒体无法让公众知道政府不愿向媒体透露的消息,所以,我坚持认为人民有权了解公共事务,媒体和政府也有责任让公众了解。当然,没有媒体和政府的合作,人们也不可能了解政府的情况。政府和媒体一次一次地没能让公众了解情况,但不能因为这一点抹杀了人民的权利。
人民的知情权这个概念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得到发展的,与此相关的书目有:肯特。库珀的《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1956),哈罗德·克罗斯的《人民的知情权》(The:People’s Right to Know(1953),以及更晚时期的奥尔森·西奥哈里斯(AIthan Theoharis)编纂的文集(保密文化)(A culture of Secrecv),《政府和人民的知情权》(The Government vs the People’s Right to Know)(1998)。此外,还有大量的文章声明这种权利的存在,并且谴责政府对这种权利的侵犯。不遵守新闻自由理论会招来公众对政府的猛烈抨击,但问题却远大于此
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牵涉到人民知情权:人民和媒体。而他们在这个主题的讨论中被省略。坦率地说,公众要不就是不知道他们享有这种权利,要不就没把这种权利当回事。看起来,他们只是毫不在意。知情权当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真有民权这回事的话。这种权利是美国政府的基石,是公众讨论,明智投票,公众观点的基石,是民主机构和民主精髓的基石。然而人们对于这项权利的关心似乎很少甚至没有。但不能因为不关心就取消这项权利。
似乎我们这个社会中惟一真正对人民的知情权感兴趣的就是媒体。新闻记者甚至被激怒,批评政府侵犯人民的这项权利,并展开热烈讨论。他们通过呼唤知情权而使新闻自由的要求变得合理。
媒体的问题是他们把否定知情权的责任全都推到政府头上。事情当然并非如此。新闻媒体本身也参与了对这项权利的否定。熟知典型的新闻操作的人一定知道:普通人只看到了或昕到了一小部分和政府相关的消息,新闻媒体于是指责政府对一些消息的省略和所犯的错误,但事实上新闻媒体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编辑和新闻主管们在提倡人民的知情权时,也在忙于选择和拒绝政府消息。他们省略这样或那样的报道、图片和观点。他们事实上是检察官——尽管有最好的出发点,但还是一名检察官。他们就如同政府官员所做的那样驾驭着新闻。他们同样扮演着限制人民知情权的角色。编辑把这称为“行使他们的编辑特权”,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进行编辑工作,而政府则是在驾驭和约束公共消息的发布。不管是哪一种文字游戏,知情权的行使都因此而受到限制。
然而媒体人一直都在呼唤知情权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权利。
观察报纸和杂志的编辑过程,你会发现官方消息被舍弃的速度快得让人吃惊。当废纸箱里装满了人们本应该阅读到的消息时,你会发现没有多少新闻人会因此伤心或咬牙切齿。新闻人批评政府隐瞒消息,却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和自己批评的政府官员一样在隐瞒消息,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隐瞒公众享有知情权。
当然,新闻人是对的,公众的确享有知情权。在美国新闻历史中,知情权一直都存在,只是在二战以前,它还没有变得如此广为人知。现在重点已经从媒体转移到了受众,从新闻自由转到了新闻责任,从媒体的机构权利转移到了公民的社会权利。这是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的部分转变。新闻的社会责任论的一部分应着眼于媒体能积极地做些什么,而不是可能被政府禁止做什么。
人民知情权是这股潮流的合理衍生物。我坚持认为民众掌握信息的需要一直是媒体自由哲学上的根本理由(最近被称为媒体的自由)。在我们这个理论上是民主的、开放的、多元的自由社会里,民众掌握信息的这种需要在哲学上被解释为一种权利。
所以,尽管丹尼斯教授提出r一些深奥的论点,其他人也否认这种权利的存在,我始终认为这种权利是存在的。不管这种权利怎样被剥夺——被政府或被媒体剥夺——它仍是美国这个民主社会的基石。它是新闻自由的理由,是美国政治保持活力的根本要求。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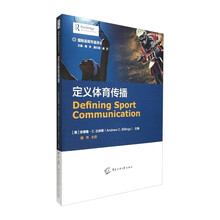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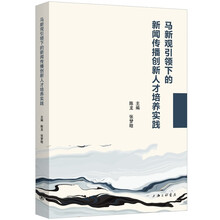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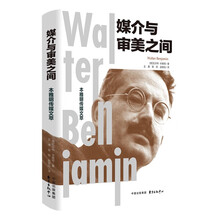

《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足根据Thomson Learning公司出版的Medtia Debate:Great Issues如r the Digital Age第三版翻译的新闻理论书籍。
本书的两位作者——纽约城市大学的埃弗里特·E.丹尼斯(EveretteE.Dennis)教授和密苏里大学的约翰·C·梅里尔(John·C.Meirill)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新闻和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出版了约70部著作,发表了数百篇学术文章。同时,他们长期以来在传播领域从事实践工作,并和业界人士保持着长期密切的联系,关注新闻传播行业的最新进展。本书立论直白,论辩有力,资料翔实,重点突出,涉及了新闻和出版自由、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媒体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全球化与新闻媒体等诸多话题,特别是关注了这些伴随着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持久话题在数字时代的新变化。形式上采用了辩论这种新鲜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考角度。
本书各章节内容安排科学合理,各章后提供了网上查询、讨论题目、研究题目等内容,适合大学本科以上新闻和传播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作为新闻理论的补充教材使用,同时也适合一切对新闻传播事业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本书由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教师和研究生共同翻译,各自承担的部分如下:吴燕:前言、作者简介、内容介绍、第1—2章;许琼莉:第3—6章;魏玉栋:第7—11章;尚京华:第12—15章;陈铎:第16—19章。全书由北京广播学院王纬教授担任审校工作。王纬教授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订。
由于时间仓促,译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