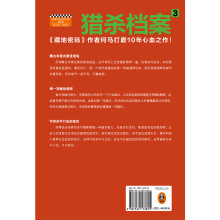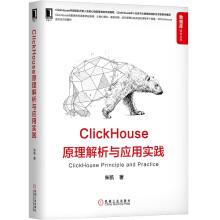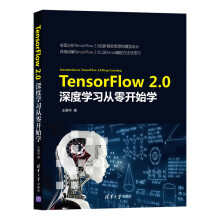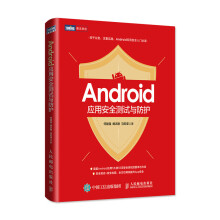葛兰西承认他的市民社会观念来自黑格尔,但他把市民社会划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是完整国家中的一部分,并且是一个创造与传播思想的组织与技术手段——这一点使他与马克思把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关系的结构的理论相区别,葛兰西不满意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生产过程看做决定社会生活所有方面这种决定论与化约论的观点,他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个部分,而且这两个部分也是相互渗透的。他说:“国家,当它想行使与颁布不受欢迎或满足于公共意见的行动或政策时,它需要组织与集中市民社会中的某些组织与要素。”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葛兰西认为,政府(政治社会)之所以能取得公众舆论和其他意识形态机构的支持,部分是由于不同阶层的精英和统治阶级共享同样的世界观与生活方式,部分是由于市民社会机构(无论他们是否直接被国家所控制)必须在统治阶级的合法统治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行动。政汉社会本身是一个国家的统治机构,它依其合法性强制市民社会的成员对它表示服从,它主要利用其包装起采的自由民主结构的外观(议会、法院、选举)来取得公众的支持,并且通过教育使民众接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政治观。而事实上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这种渗透,并不必然都是反抗的,因为市民社会中的霸权组织,如政党和有组织的教会,往往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条件下,变质为统治阶级国家机构中的一部分。葛兰西认为,正是这种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复杂联系,正是这种强制与同意的共同默契,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葛兰西实际上强调的是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统治产生同意的过程。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首先要在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中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最后重新把政治社会吸收到市民社会中去(也就是达到马克思早期所坚持的理性国家的状态),最后,随着市民社会的扩大,当市民社会占领了政治社会时,政治社会就消失了。葛兰西这样写道:“作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因素(即作为一种创造新文明,新型的人及新型公民的运动),可以使国家和个人(某个社会集团的个人)保持一致,这一论断必须有助于下决心在政治社会的外壳里建立一个既复杂又井然有序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个人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而又并不因此而同政治社会相抵触,相反,倒是它的政党的延续,有机的补充。”
如果说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所施行的地方,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是否完全就是一些市民社会中的精英(或共产党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灌输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葛兰西由于同时强调阶级意识的外部灌输和自发形成而与列宁的观点有所不同,因为虽然列宁也强调社会主义思想要由职业革命家从外部灌输到群众斗争中去的看法,但他认为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制度与思想的束缚,不会自发产生革命信仰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只可能产生一些为改善局部利益进行的反对工厂主的罢工运动——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假如我们说,葛兰西在强调阶级意识的“自发性”这一点上与列宁不同,那么他与马克思的区别又表现在哪里呢?下面,就让我们先考察一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观。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会形成革命的意识,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紧张冲突与对抗,工人阶级必将理解他们悲惨的生活条件及被资产阶级统治与压迫的事实,从而自然会在革命中形成共同的革命意识。革命是阶级意识形成的学校。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 “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和资本家的剥削,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的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这种联合的发展壮大能够形成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意识,所以说,资产阶级的生产与剥削,造就的正是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形成。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形成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必将出现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又是这种意识形成的必由途径。当然,一批在工商业的竞争中失败的资产阶级成员和在革命斗争激化时叛变资产阶级的成员,他们转入无产阶级队伍,也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教育因素,促进了革命意识的形成。
这样,我们看到,假如说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谈阶级意识,从而使他带有认为这种革命意识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和不可避免的倾向的话,列宁则明显反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自发性,而葛兰西似乎又是综合了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与列宁一致的是,葛兰西也认为工人阶级的意识不能完全自发地从生产环境和阶级斗争中产生,它需要杰出精英从外部系统把革命意识灌输给群众,形成为群众意识。他这样说:“自发性的要素对革命斗争是不够的,它永远不能导致工人阶级超越现有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需要的是‘自觉’的要素,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的要素,懂得斗争的条件,工人生活中的社会关系,那些关系起作用的主要倾向、社会中由于不能解决对抗存在而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等。”但葛兰西也不是完全否认自发性,他与马克思有某种程度上的默契,因为他同时也认为,革命意识不仅是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的,它也是无产阶级经验所固有的,“它大部分是从群众本身的自发冲动、见识和能力,从内部提炼加工而成的”。群众本身所拥有的一些意识,是一些“常识”,即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未加批判的世界观,这种常识不是完全被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同化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一种既包含真理成分,又大多数以未加批判的论据为基础的从属阶级的世界观。葛兰西认为,常识也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它需要知识分子在同普通人的接触当中利用“文化领导权”或“实践哲学”以系统的、融贯的和批判的方式进行改造,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既要承认自发“常识”的片面合理性,又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引导和批判。葛兰西正是用下面这段话表明了这层意思:“创造一种新文化,不只是意味着人们自己个人的‘独创’发现,它也——而且最特别地——意味着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散播已经发现的真理,可以说是这些真理的‘社会化’,甚至使它们成为重大的活动的基础,一个协调的和智力与道德制度的因素。因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考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发现还是智识分子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