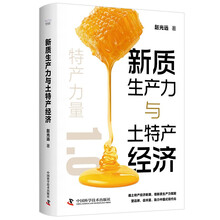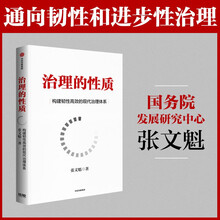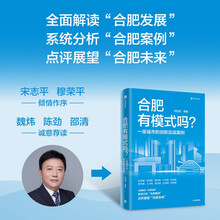出生地、居住地和社会变迁
在19世纪,绝大多数汉口人与此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外地人”。我们在这一章讨论了这些人来到汉口的原因、城市中地方“亚族群”的构成、对所认同的家乡地区的联系程度,以及拥有共同出生地的同乡人之间的情感。在继续讨论建立在“亚族群”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之前,让我们再简单考察一下汉口的移民和寓居者对他们自己作为“汉口市民”的认同程度。
至少从社会活动的参与方面看,汉口寓居商人中的头面人物都把他们自己看做全面融入汉口社会的一分子。县志的人物传和当时其他的一些资料都赞扬了许多非汉口人在当地的慈善之举:资助水利工程以及其他的建设项目,在洪水、饥荒或兵燹后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宿,设立免费的救生船只、孤儿院、学校、医疗服务以及消防队,参与综合这些服务的各种善堂的建设。民国《夏口县志》有一章专门记录了一些出手大方的寓居慈善家。水灾和火灾的隐患,以及社会动乱的危害,无疑是激发他们这些活动的契机;但是,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似乎也起到一定作用——如县志记载,有时个别富有的盐商或其他行业的商人由于过于乐善好施而耗尽家财。
在军事战乱时更能证明寓居商人是极力维护地方利益的。当汉口受到白莲教徒、太平军、捻军袭击时,许多外来商人,并没有逃回家乡,而是组建城市团练,修建防御工事,有时甚至是献出生命以尽忠。在19世纪80年代城市安全受到威胁之际,在汉口的寓居商人比本地工人和小商贩奉献得更多,他们一直在城市中留守,并参与防御。
在职业事务方面,地方上活跃的商人可能将他们的利益直接和汉口的事务挂钩,而不是和他们所隶属的家乡地区的事务相联系。我们先前论述的盐贸易表明,汉口的盐商喜欢和当地官员,而不是两淮盐业中心的官员合作;南京的一些盐务官员三番五次挑起商人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武汉的官员则仰赖商人的财富,与他们结合,或者不愿冒疏远这些武汉社会的中流砥柱所可能有的风险。就商人自身而言,虽然他们来自其他省份,但他们更愿意把商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投入到他们工作、生活、成家的地方,而不愿意花在长江下游地区官府假借朝廷名义巧设的各种名目上。
何炳棣对汉口和窦季良对相类似的重庆的专门研究,都认为寓居者的情感和个人身份认同感都倾向于客居的地方。何炳棣说:“不同省份与地区的商人在汉口经营商业到一定时期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和汉口地方社会建立紧密联系。”窦季良则描述了在一个寓航海发展取向的囤同乡基础之上的亚社区(乡土)对群体利益的自觉不断扩展、逐步融合成复合式社区精神的过程。
汉口寓居者通过个人的号来表达他们对汉口文化的认同,如孙楚池(湖北的池塘)、徐临汉(靠近汉口或临近汉水)、汪会汉(在汉口相会)。同化的另一个更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寓居者经常娶本地女子或其他客居人的女子为妻。我们已看到,许多人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入籍汉阳,都在汉口建立宗族的支系。一些家族,如来自徽州的汪家的几个支系,在汉口的居住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他们仍愿意做“寓居者”。这些家族的子孙从来没回过家乡,他们在客居城市成长,一生都和当地的绅商打交道。几代以后,许多家族逐渐衰败,开始融入汉口的一些下层民众。但是,即使那样,他们也可能会保持某些身份特征以及对故乡的感觉。
马克斯·韦伯所建立的中国城市理想模式,最具代表性地说明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的认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报道而认为城市的大部分人口都是由移民和对家乡地区仍有深厚情感的寓居者构成。在提出中国城市类型单一或只有历时性变化这一假设性论断的过程中,韦伯概括说:中国城市居住者对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没有什么情感认同。后来的一些社会学家也进一步论述了这一观点,他们甚至在最近还强调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非官方的“逃避法”,它在事实上给那些雄心勃勃地往上爬的人,提供了一个逆城市化的自由天地。例如:在日本,负责任的城市意识有发展,有利于“现代化”,它促进了“乡村地区的(商人、工匠)和武士的永久性迁出”。这和中国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的绅士、商人、工匠常常是在城市里赚钱,然后回到乡村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城市使它们的寓居人口脱离乡村的束缚和宗族的精神压迫;另一方面,却又以“亲族”和同乡关系为基础,在城市里建立起特殊的“亚社区”。
他们对户籍的态度表明,帝国晚期城市居民能冷静地更实际地看待他们对家乡的奇特依恋之情。一些汉口家族的历史证实了施坚雅的推测:“在城市居住的几代时间以内,家乡的特征还是很明显。”从他们参与各种慈善活动和公益事业中可以看出,他们越来越认同自己的客居地方身份。但是,至少是为了一些功利目的,如找工作或获得城市里同乡的物质和金钱帮助,多数非本地的汉口居民仍和家乡地区保持联系。
政治学家罗伯特·梅尔森(Robert.Melson)和霍华德·沃尔普(Howard wolpe)在一篇探讨文化各层级的论文中,简洁地阐释其观点说:“共同的变革使得社会身份逐渐层累而不是替代。”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城市居住者对家乡身份的认同——可以称作他的“出生地身份”(native identity),就一定会阻碍他成为移居或寓居的地方社会中的一员——可以称作他的“居住地身份”(locational identity)。于是汉口的一个徽州人可以很轻易地成为汉口人,而不必取消他作为徽州地方经济社会体系中某一地方人的身份特征(事实上,许多汉口寓居者私下里仍想要合法地保持这种多重身份)。这种居住地身份的发展促进了菲利普·柯亭(Philip curtin)所说的“地方团结”——一种在城市居民中普遍存在的情感——的形成,而这种“团结”,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在19世纪汉口社会中越来越突出、明显。
最后,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梅尔森和沃尔普将身份的层累分成“共同的变革”和“社会流动”两个时期。在各种文化背景里,特别是在发生重要社会变革时期,各种各样的、“自我觉醒的”“亚族群”人口之间的相互交往,似乎是商业中心城市所特有的现象。例如: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对发展中的印度尼西亚城镇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50年代,这些城镇主要接纳一些“高度职业化的小商人,他们形成紧密结合的地方群体,以专营某一类贸易”。中世纪的伦敦也是由不同郡份的商人阶层占主导地位,他们在参与建设一个强大的商业都市和为他们的客居城市赢得革命性的政治权力而激烈斗争时,仍和家乡地区保持联系。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这种个人身份的层累以及由此引起的“亚族群”之问的竞争与合作,是19世纪汉口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