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论和其他逻辑方法
“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因此苏格拉底会死。”就让我从这个恰当且著名的(尽管,我们有时会注意到,这并不是标准的)三段论开始。这一论证的有效性——而不是结论的真实与否,结论真实与否取决于大小前提是否真实——看上去令人完全信服。但这只是因为这个结论,即苏格拉底会死,是包含在大前提对“人”的界定中了。这个前提实际说的只是:这里有一个贴了标签“人”的箱子,箱子里有一些东西,其中每一个都“会死”。小前提则告诉我们,箱子里的东西都有个名字牌,其中有一个牌子上写的是“苏格拉底”。当我们把苏格拉底拿出箱子时,我们就知道他是会死的,因为箱子里惟一有的东西都是会死的。因此,我们拿出来的不过是我们预先放进去的东西。
于是,通过一种隐喻,一个箱子的隐喻,我们发现三段论有很令人信服的有效性。(这看起来也许很奇怪,一个人对逻辑的信任竟然是由一个隐喻支撑的;然而,这已经显露出逻辑的有限性和隐喻在认识上的重要性。)而当我们离开诸如三段沦这种最简单、最明显的逻辑推理的例子时,这种推理的性质和融贯力就变得不那么明确了。我们认为,2+2=4的命题根据其定义就是真的,就像苏格拉底会死的命题一样,也是根据定义就是真的。但由于在这个数39字的例子中,什么是那个“箱子”,其中装的又是什么,都不明确,因此就不能再用这个具有包容力的隐喻来保证我们信服逻辑推理了。而且,一旦我们开始提出复杂的数学问题,诸如是否每一个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例如16就是13与3之和),我们就进入一个领域,在这里没有机械的、断然真确的决策程序可供利用,而问题却又很难、很不确定、外行人无以进入,就如同那些与概念、定义世界不同的经验世界中最棘手的问题一样。事实上,如今已经证明数学不可能简约为逻辑。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边,而紧紧抓住最简单的法律推理,因为除极少数特例外,法律人使用的只是这种法律推理。
三段论的推理非常有力,又为人熟知,因此,渴求自己的活动看上去尽量客观的律师和法官都花费了很大力气使法律推理看上去尽可能像是三段论。而过分使用三段论恰恰是受到霍姆斯抨击的那种法律形式主义的最根本特点。但是,今天,被当作贬义使用时,“形式主义”更可能是指过分相信制定法和宪法语言的透明性,并因此过分相信疑难解释问题会有定然正确的答案,而不是指大量使用三段论。被当作非贬义使用时,形式主义可能指一种强烈的(这种强烈或许是正当的)确信,即可以通过常规法律分析手段获得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常规手段主要是指细心阅读文本,发现其中的规则,然后从规则中演绎出具体案件的结果。或者,形式
主义也可能仅指运用逻辑从前提推导出法律结论。
形式主义可谓风情万种,但是,它的最有用的意义是从形式和实质的反差中引申出来的。形式指的是法律内在的东西,实质指的是法律外部的世界,就像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差别一样。法律的自足性和客观性是通过仅仅在形式层面分析法律来保证的,这一层面的分析只要求探讨法律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当法律的结果取决于与现实世界有关的事实之际,法律的自足性和客观性就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些事实可能有争议,或者是与创造或解释规则相关的社会事实或伦理事实。由于逻辑推理探讨的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形式(实质意义上的)形式主义与逻辑(数学意义上的)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很清楚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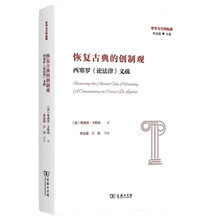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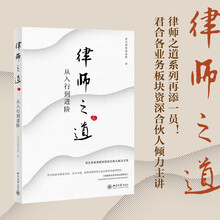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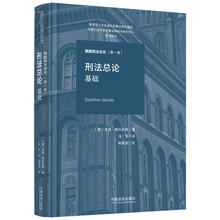




一
这套译丛是一个很长过程的积浞。
我从1993年开始翻译波斯纳的著作,这就是1994年出版的《法理学问题》。此后多年也读了他的不少著作,但是这位作者的写作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因此至今没有或没有能力读完他的全部著作。但是自1996年起,鉴于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视野狭窄和普遍缺乏对社会科学的了解,缺乏人文学科深度,也鉴于希望中国的法官了解外国法官的专业素养和学术素养,我一直想编一部两卷本的《波斯纳文选》。在这种想法指导下,同时也为了精读,我陆陆续续选译了波斯纳法官的少量论文和许多著作申的一些章节,包括《超越法律》、《性与理性》、《法律与文学》、《司法的经济学》等著作。到1998年时,已经译了80 万字左右。也联系了版权,但最终没有落实,乃至未能修改最后定稿。初稿就在计算机的硬盘上蛰伏了很久。
1998年,我感到自己《法理学问题》的译文问题不少,除了一些令自己难堪的错失桩外,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翻译时刚回国,中文表达比较生疏,加之基于当时的一种奇怪观点,希望保持英文文法,因此译文太欧化,一定令读者很头痛。我为此深感內疚,并决定重译该书,到1999年上半年完成了译稿。
1999年lO月,我到哈佛做访问学者,更系统地阅读了一些波斯纳的著作;并同样仅仅是为了精读,我翻译了他当年的新著《法律与道德理论的疑问》。此后,由于《美国法律文库》项目的启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又约我翻译波斯纳的《超越法律》全书,我也答应了。诸多因素的汇合,使我决心把这一系列零零碎碎的翻译变成一个大的翻译项目。
2000年5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葛维堡教授和欧文。费斯教授的大力安排下,我从堪布里奇飞到了芝加哥,同波斯纳法官会了面,其间也谈到了我的打算和决定。临别时,波斯纳法官同意了我的请求。
2000年8月回国之后,就开始了一系列工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社长李传敢、编辑张越、赵瑞红等给予了积极并且是很大的支持。会同出版社一起,我进行了很麻烦的版权联系和交易。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忙里偷闲,特别是利用寒暑假,进行翻译,并组织翻译。因此,才有了目前的这一套丛书,完成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二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这套文丛似乎完全是一个机会主义过程的产物,甚至,挑剔一点说,未必我就没有减少自己的“沉淀成本”(Sunk COSt)的意图。但是,总的说来,这套书的选择是有策划的,有斟酌的。
如同上面提到的,我的选译是有针对性的,一是针对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二是针对包括法官在內的读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