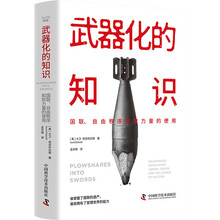首先必须活下去。<br> 必须闯过心肌梗塞这一关,必须活下去。第一步哪怕是战胜虚弱无力,恢复知觉也好。我躺在病床上:右手扎着输液的针头,左手也绑着一种叫不出名的“可爱的东西”,头都不能抬一下。只能老老实实地躺着,完全与世隔绝,就像国家总统后来一再表白的,他在天堂般的福罗斯的处境一样:电话、广播、电视全都哑巴了。而医生护士们仿佛达成了默契,只重复着说:您不能激动,您需要静养。<br> 几个月之后,当我以俄罗斯总统候选人身份,被迫投入快节奏的竞选活动时,某些很讲民主的报纸居然登出了这样的马路奇谈:雷日科夫真的得过心肌梗塞吗?瞧他在电视上的那副精神,每天发表演说,还周游全国呢!甚至还引用几位患过心肌梗塞的病人的来信,愤怒地说:三年前我得了心肌梗塞,至今未愈,而这位……仅仅出于最起码的礼貌才未说出“雷日科夫在装病!”在公开性时代,已无礼貌可言,在许多记者以及不仅是记者看来,公开性就是可以为所欲为。<br> 我活过来了,痊愈康复并努力忘却疾病,这难道有错吗?为什么要这样搞,问问医生岂不一清二楚。当然,也可以在这里列举我的病历、心电图和化验单,可是,委婉地说,恐怕不是每一位读者都感兴趣。 我只说一点,患病初期的确不妙,不是一般的不妙,甚至有点可怕:这也许是因为,我一辈子除了感冒,还从来没生过病,从未体验过卧病在床的滋味。所以我无条件地听从了医生的吩咐,毫无反抗地同他们达成“默契”,甚至同自己的妻子——我被隔离之后,她就想闯进病房看望,哪怕看10分钟也好,——也不讨论任何严肃的问题。<br> 总之,度过特别严重的最初几天之后,医生们肯定地答复说:再过一个月您就能自己走出医院了。我相信这话。果真,一个月之后,怀着对所有用学识、经验、关怀和人道主义延续我生命的人的难以言状、终生不忘的感激,我出院了。此外,我深信,我之所以能够康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在乌拉尔机器制造厂极其忙碌、极为美好地度过了极其忙碌、极其美好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该厂锤炼了我强健的体魄,我没有时间生病,也没有学会生病。<br> 本来,不值得为我的病情耗费这许多笔墨,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有人在需要时还不时地端出这道并不新鲜的菜肴。而在我康复的那些日子里,妻子给我往医院带来的是大量友善、感人的信件和电报。写信人分布在苏联各地——有老有少,有熟有生,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有中小学生,也有大学生。接收地址基本一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我珍藏着数千份这样的电报和信件,它们在我一生中大概是最困难的时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br> 我是12月25日夜里住进医院的。过了两个星期,即1991年1月10日,主治医生来到病房,试探性地问道:<br>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来探望您?”<br> 问题提得真有意思!在我的印象中,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还从未如此客气过。<br> “这不由我做主,”我答道,“您来决定:可以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br> 然而我心里却想:越早越好。我坦诚地认为:即将进行的谈话对他,对我都是不愉快的,却又是不容回避的。<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