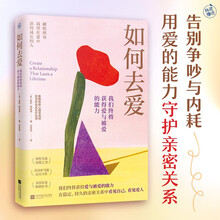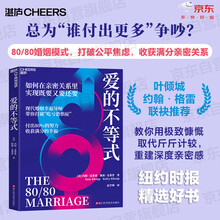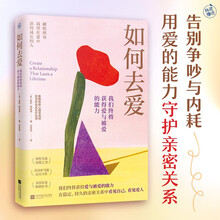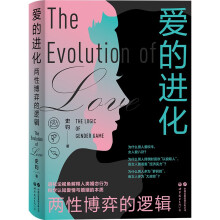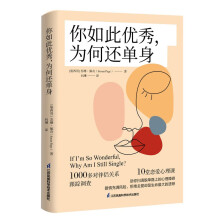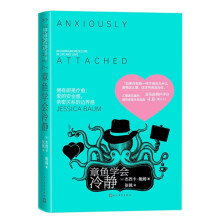黑格尔在此首先明确指出妇女不能进行高深的创作,不能从政;然后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妇女缺乏“一种普遍的东西”,而且这种缺乏他“不知怎么回事”。一个世纪后,罗素对此做了简要回答:“最初,人们只是蒙蔽女性,因为人们希望她们的无知能有助于男性的支配地位。然而,妇女竟然逐渐安于这种观念,认为无知对于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正是由于男性这种有意的蒙蔽,致使女性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各个方面都缺乏“一种普遍的东西”。这种蒙蔽在中国一度变成真理,“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最经典的表述。
这样,过去在知识领域,女性几乎没有一席之地,有的只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肤浅”的呻吟,而比较抽象的哲学等领域一直由男性独领风骚。这严重地限制了女性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所以可以说,人类的哲学就是男人的哲学,中国哲学就是中国男人的哲学。
这种人为的限制,留给女性的是什么呢?那便是红尘中——物质世界——打扫不完的灰烬、繁重的家务及传宗接代的重任,现在又加上养家糊口。女性在精神上丧失了本体与自我,忙完了家务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注重实际、爱慕虚荣。这使男性要不断追逐更多的名利,以满足女性的这种嗜好。“金钱意味着能带来欢乐,因而,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商人重利轻别离”,过去君子重名、小人重利。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渴望的是名利双收,所以追逐名利的广度深度都有所拓展,“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可以说,目前人们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是围绕名利展开的,每个人都像《林冲夜奔》那样,惶惶然不知所归,上得山来最终的结局是被招安,招安之后是否幸福不得而知。
当然,注重名利并非坏事,它可以促进物质和精神生产,使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一切以名利为标准来衡量,那就会物极必反。
虚荣往往在攀比中无限升级,最终形成一个个黑洞,吸尽男性所有的精力和心血,使他们丧失了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感受,甚至丧失人性,走向犯罪。据调查,大约95%的贪官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女人的影子。罗素在中国时已注意到这种情况,没想到时隔大半个世纪,又旧事重演。“在中国,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收刮大量钱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身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当然,他不会一个人往国外安享晚年。”但随着中国法制的健全,“走为上计”正逐渐失效,所以名利双赢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女性虚荣心的鼓励下,男人不仅成了一种“普遍的”赚钱机器,而且成了更为片面而不是“普遍的东西”,所以,这种蒙蔽女性的做法对男性来说实在是一种潜在的禁锢。我国一位著名男性计算机专家就曾撰文细数自己“寂寞深闺”的幽怨:“我已成了妻子家族中光耀门楣的一块‘牌子’,这牌子我还得打下去,为了这,我告别了梦萦魂牵的贝多芬,投身到计算机世界……计算机是智能化的机器,我是机器化的智能人……我渴望解脱,撕碎我头上的光环,去享受人生、回归自我,去拥抱贝多芬,拥抱大自然。”大概许多成功男性都有同感,这说明双重标准并没有让男性过得痛快。
男性注重名利的结果使女性也步人这一误区。重名轻实,唯名是尊,使中国女性忽视婚姻的实际质量,可容忍与不可容忍的、合理与不合理的都一并承受下来,关键是要有名份,其他都是次要的。“三个女人一台戏”,所以,在过去的三妻四妾,如今的大奶二奶三奶四奶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普遍地存在着。这使得各种情杀案、女性犯罪不断升级。两败俱伤甚至多败俱伤的情况比比皆是。
总之,由上述可见,从道德世界到审美世界再到抽象世界,女性由被动的道德实体渐化为审美的载体,并最终在玄奥的哲学世界里幻化为虚无的存在。这就是说,在存在的最高境界里,人类已由双性繁殖演变成单性繁殖了,由双性动物退化到单性动物。这种片面性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实行双重标准,表面上看是严重侵害了女性的权益,但从长远看,真正受到损害的是男性自身,是整个国家的发展。叔本华也指出:妇女的家庭可以被打碎,但妇女的自我尚存,它不可能被粉碎。妇女不仅要追求生活的自由,反对男人对事业的垄断,而且要反对男人对文明的垄断,这种垄断打击着妇女的灵魂,并且吞噬着她们的生命。妇女必须依靠自己,全力投入人类世界的创造,以恢复倾斜的社会平衡。
朝向我们的身体与阅读者之间的这张脸,于是呈现出百变情绪,星光点点,曲折斑驳:无可奈何的,蛮力切人的,下意识的,自觉自愿的……
联想细胞过度发达的读者自然想到将这一关系与性爱关系比附:勾引、挑逗、半推半就、投怀送抱……当然也有下三滥的强迫、威胁或迷香。
然而对身体的阅读绝不止于性爱,阅读身体岂是性爱能够包容得了的!
红袖添香夜伴读,耳鬓厮磨,长相厮守,相对白头,一份恬静温心之美——扉外严霜,辣雪,陨石,地陷;户内两人自成世界,静下倾听,天再变,心犹温。
暗香盈袖,暗暗的香粉纵然深埋水袖,多事的鼻息还是穿透雾障,直人藕花深处,嗅得一笼烟水、一笼纱洗的女儿香。官能也许魂不守舍了,忘记了居所,在香的边缘滑移,滑移。
蓦然回首月明中,是心悸,是发现的电光石火,仿佛平地起惊雷,梦过多少回的底片一下子显影定型而固定下来,梦圆其实同时也是梦破的另一种读法,梦跌落到现实的街口,五彩顿为黑白。
墙内秋千墙外道,多情却因无情恼。佛说:风动?帆动?风不曾动,帆不曾动,施主心在动。看风景的蓄满蓝汪汪满眼情思,或者乐山乐水,或者随物自在,都是一厢情愿,风景根本没有寓人一根情丝、一抹表情:墙内笑语墙内红杏,自闹自的春,自开闭自家花床。
人面何处桃花杨柳,杨柳情性随风,,桃花骤开易老,都不好作长久计议。何况一侧身,一颦眉,一愣怔,转身闭眼愣神前的分明所在居停的早不是当日情趣、那时光景……
念来怅然。
然而,在对他人身体的阅读上,人们总是不觉厌倦。上帝赐予的这本好书——据说人类还有一个雅号叫作“万物灵长”,既然掌领万物,自然有高出万侪的智慧,动辄役使,动辄愚情;自然有美过万类的身体——因为通俗,人人都以为已然读懂,或者至少,也有望读懂。岂知诸般读法,难得不生吞活剥,好读书不求甚解,了悟星点,又似乎点墨全无;断章取义,完整的一本大书被强力肢解,张大一对探照灯,只聚光阴私;也少不得莫须有式添枝加叶。任意涂抹;误读自是常态,打着阅读的幌子的伪读者也不鲜见,千姿百态,不一而足。
问题不在于这些真正实行了阉割手术的人们——他们在数量上的有限,很容易使得人们把这种现象只与一个人口上的少数相联系。比阉割的人口分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制度,是这个社会所有男性都同意、认可并参与、巩固、强化的一种体制。这种制度承认并一再复制这样的神话: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男人面前,其余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让步;那些尚未被阉割的男人,将尽一切可能满足那个唯一的男人的需要,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被阉割的焦虑”就不存在于符号或者想像之中,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比照已经被割掉生殖器的太监,这些人只是暂时替皇帝保存这些东西而已,从本质上,它们不属于他本人。或许是因为受罚,或许是出于效忠,一旦皇帝有这样的需要,那么,他将随时奉献出来,没有后悔的余地。迄今皇帝还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仅仅是皇恩浩荡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宦官制度并不是那个社会制度的不起眼的附属部分,而是它的表征乃至核心所在。否定一部分男人(太监)的性别身份,实际上是否定除了皇帝之外其他所有男人的性别身份:至少在皇帝面前,其余的男人都是“次男人”、有待完成最终的阉割手续。因此,“净身’’就不仅是发生在一些男人肉体上的事实,它也发生在其余男人的意识当中。当一些男人身体上遭受阉割之时,另外一些男人在精神上、人格上、尊严方面就毫发无伤么?被割掉的男根是个空洞,另外一些男人虽然挂着那个东西,但也是徒有其表而已,对许多人来说,它仅仅意味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当然,这套逻辑适合于自愿加入这套游戏的人,适合那些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贫贱地位,想要在险恶的朝廷官府当中谋求生存和权力的人们。应该说,传统封建制度中的皇帝并不直接召唤每一个人,只要不犯上作乱,你是井水,皇帝是河水;但是那些不甘居人下,想和皇帝同饮一江水的人就不一样了。接受皇帝询唤的人,他们想要在这种等级制度中获取一个位置,皇帝对他们的要求便是制裁性的:必须把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除去自身的一切私心杂念,以便让自己成为皇帝意志的跑马场。由于其结构具有金字塔的性质,处于这个等级制度上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它上面的更高一层,因而它自身仍然是易受攻击和面临威胁的。我完全不想用“女人”这个词,但是在那种权力游戏中,皇帝和臣子的关系,经常被比喻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净身人宫的男人在有地位的太监的引领下,要立下“婚书”,即把自己当作女人一样“嫁”到宫里去;而一些得不到皇帝重用的男人,会把自己比作迟暮的“香草美人”或者“宫廷怨妇”,抱怨皇帝不来垂青他们。这种现象拿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是无法解释的,那里有一个“菲勒斯中心”,即男根中心。但是在中国,即便是男根,也不是牢不可破的,它时时处于被阉割、被削弱、被威胁的危险之中。对许多男人来说,这个表述改为“只有一个男根是中心”更为恰当,而他们自身,则处于“去势”和“非雄性”之中。
如此牺牲,所换来的回报是相当可观的。中文中“出人头地”是一个难以用西方语言对译的一个词。与它比较接近的是ambition,即“野心”、“抱负”,拥有ambition的人虽然不安分,但是他所要实现的是自己的某个目标,一旦自己的某个梦想成为现实,这个人就有成就感,就会感到满足,他以自己的尺度衡量自己的成功。而对于想“出人头地”的人来说,其奋斗的目标在于获得一个“人上人”的身份;他需要在与别人相比当中,证明自己是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他需要时时有人仰视他,有人艳羡他,承认他是如何了不起,如何能够超越许多人,一跃而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换句话说,出人头地需要有人围观,荣华富贵需要有人在场。这是一种奇特的精英意识,所依据的不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或者贡献,而是被他人知晓、自身出名的程度。所谓人和人之间的真正平等,这种平等的根据何在,对这样的精英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除非出人头地,否则便一无是处;除了能够高居人上,否则便一无可取。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若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