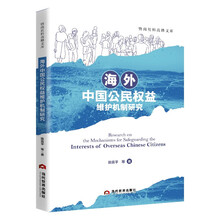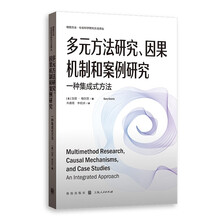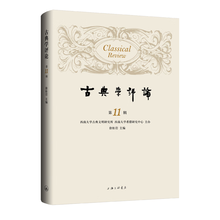事实上,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个具有批判性涵义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基础当然是对话,如果有一个共享空间,相互间的交谈就可平等地开始。哈贝马斯没有满足于1962年即已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而是在此后的一系列研究中将法律、道德、政治一齐纳入其交往理论中。他在]992年出版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一书中,展示了他极为广阔的现代视野:“只有在现代中,政治统治才可能以实证法形式发展成法律型统治。政治权力对于法律之内在功能的贡献,也就是对于行为期待之稳定的贡献,就在于确定一种法律确定性。”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法律也必须作为正义的来源而始终在场。但是,如果法律被用于任何政治理由的话,这种正义来源就会出现枯竭”。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和“交往权力”同源地产生于那种众多人公开地赞同的意见。他的这种将政、法、德系统观之的“交往理性”,对于当代数字化生存走向是极有启示意义的。毕竟,“构成生活世界的,是一个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中分叉开来的交往行动网络。生活世界对文化信念和合法秩序之源泉的依赖,不亚于它对社会化了的个体之认同的凭靠”,而“社会化了的个人,若无法在通过文化传统而表达的、通过合法秩序而稳定的相互承认关系中找到支持,就不可能作为主体而维持自己一一反之亦然。作为生活世界之中心的日常交往实践,同源地来自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社会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社会和人格互为前提”。在道德文化整体中,法律既是知识系统又是行动系统。显然,“数字化生存”的挑战,要求我们以新的人文价值观转换的成功,来获得新生活方式的建构性调适。
2.全球化生存与个人化时代的统一
在尼葛罗庞帝看来,数字时代的特征,是大众传媒这一公共领域的覆盖面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所以他向人们宣称: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