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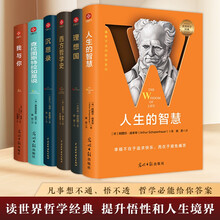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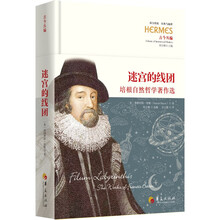

我们可以说,在柏拉图那里,关心自己与关心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大致是通过三种方式确立起来的。或者,让我们回到我随后要对你们说的内容上,在柏拉图那里,认识自己是“关心你自己”的普遍的和根本的律令的一个方面、一个要素、一个形式——毫无疑问是主要的,但只是一种形式。新柏拉图主义颠覆了这一关系。但是,反过来,在柏拉图那里,泻药与政治不是相互区分开来的。相反,泻药与政治属于同一个方法。这有三种方式。因为人通过关心自己(这是我刚才对你们说的),会使自己能够关心其他人。可以说,在关心自己与关心其他人之间存在一种目的关系。我关心自己是为了能够关心其他人。我将让自己服下新柏拉图主义者说的“泻药”(katharsis),我将用这种泻药方式,以便能够成为一个政治主体。政治主体是指:知道什么是政治的人,能够统治的人。第一个关系是目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一种相互性关系。因为如果通过关心我自己,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意义上用泻药来净化自己,那么我就会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对我所治理的城邦做了善事。如果通过关心我自己,我向我的同胞们确保了他们的获救、财产和城邦的胜利,那么反过来,我也会从我所确保的大家的财产、城邦的获救、胜利中受益,因为我属于这个城邦的共同体。在拯救城邦中,关心自己获得了补偿和保证。人也就拯救了他自己,因为城邦得救了,因为人通过关心自己而让城邦得救了。这种循环明显地出现在《理想国》的整个结构中。最后是第三个关系,在目的关系与相互性关系之后: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主要蕴涵关系。因为灵魂是通过关心自己、实行“净化自身”(这不是柏拉图的用语,而是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术语)才同时发现自己是什么和自己知道什么,或者说:它一直知道的东西。而且它还同时发现了它的存在与它的知识。它发现了它是什么,以及它发现了它在回忆中所沉思的东西。它因此能够在这种回忆活动中直达对真理的沉思,从而重新公正地确立城邦的秩序。由此看来,在柏拉图那里,存在三种联系、承载新柏拉图主义者所说的泻药和政治的方式:即政治技术中的目的关系(我必须关心我自己以便恰当地了解让我可以关心其他人的政治技术),城邦形式中的相互性关系(因为我通过拯救自己而拯救了城邦,而且,我通过拯救了城邦而拯救了我自己),第三是回忆形式中的蕴涵关系。这就是关心自己与关心其他人之间的大致关系,这就是在柏拉图那里所确立的关系,而且牢固的难以解开。
不过,如果我们现在置身于我确定的时代(也即公元1—2世纪)里,那么这种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除了。看着自己慢慢摆脱束缚(以及修身的技术和被柏拉图认为是关心自己的修身实践),作为一种自足的目的,而关心其他人则非终极目的和可以让人强调关心自己的指引,这也许是修身实践历史上和古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第一,人所关心的自己不再是众要素之一,或者,如果它看上去是众要素之一,那么你们将会看到这——点,也即在一套推理或特殊的认识形式之后。人所关心的这个自己不再是一个铰链。它不再是一个驿站。它不再
是一个转向其他事物(城邦或者其他人)的要素。自身是关心自己的确切的和唯一的目标。因此,这种活动,这种关心自己的实践,决不能被认为纯粹是为关心其他人做准备的。这是一种只
以自身为中心的活动,而且只在自身中,也即在修身活动中达到自身圆满的活动。人是为了自身而关心自身,而且,这种关心只有在关心自己中才达到对自身的奖惩。可以说,在被称之为关心自己的实践中,既有把自身抽象化(请原谅我用这个词)为关心的对象,又有自身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一言以蔽之,在柏拉图那里,关心自己显然是向有关城邦、他人、“政治”(politeia)和公正(dikaiosunê)等问题开放的,它是自身封闭的(至少在我所说的公元1&2世纪里初看上去是如此)。以上就是现在必须详细分析的现象的一般曲线,因为我向你们说的一切既是真的,也是假的。我们认为这在某个层面上,从某个角度来看,并有所跳跃后才可能是真的。总之,我认为摆脱被新柏拉图主义者一再说成是泻药的东西(相对于他们所说的政治)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之所以是重要的现象,有两个或三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