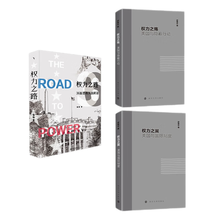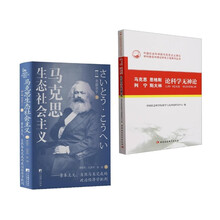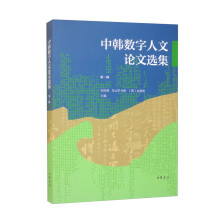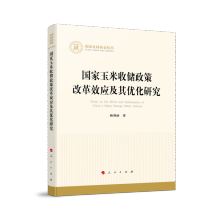《问路集——重构一种新阅读—批评视界(上)》:
只有从根本处的反思和批判,我们才会正确地理解与解释种种文化现象与事实。譬如话剧艺术,对我国而言是门年轻的艺术类型,它是伴随着五四运动而被引进来的,在发展的初始,呈现着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气质和态势,各种戏剧的思潮、流派、方法、风格均被广泛地介绍、学习、借鉴,剧作家们尝试着用不同的原则、不同的手法写戏,如郭沫若创作出表现主义格调的剧本,田汉创作出象征主义倾向的剧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戏剧形成了多方位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在嗣后的进一步发展中,“百花齐放”的可喜氛围却演变成另一种单一格局。在创作原则与创作方法上,除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得到首肯并被广泛采纳外,其他诸如表观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均日渐式微,终至销声匿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一次“拒绝阅读”现象,绝非出自某一外在权威的敕令,或屈从于某一外在的淫威压力,而是人们内心的意愿、崇高的使命感、最高的道德律令使然。有目共睹,五四运动以来的这一代人,眼界并不狭隘,心胸并不闭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大都西渡东渐、学贯中西、满腹经纶,论才学、论志向,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都可称得上是英才俊杰。然而,沸腾在这一代人心中的,大多是那熔岩般奔突不已的政治激情与救亡意识,文人雅士与实际政治家的合一,在新时代的特殊环境中,再度成为一代文化精英的命运。而且,像我们民族历来的文人那样,从事政治才是自己的人生正途,而舞文弄墨则是从属于政治生涯的雅兴而已。像历来的文人那样,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艺术若要获得严肃性、崇高性,亦只有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文化的启蒙职责,亦仅仅旨在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同仇敌忾的斗争意志,而唤醒人内在的能力、才华、热情,诸如思维、情感、想象等则始终被摒弃在启蒙之外。诚然,时值国破家亡、民族危难当头,怎么可能有闲心逸兴去追寻什么个性生命的全面发展呢?此论不能不说言之有理,然而,只要我们再将眼光打开一些,便会发现,这一真理仍然是相对的,在它里面蕴含着谬误。任何生命均有其长度与强度两个方面的价值与生存意义,倘若仅有长度而没有强度,那么无异于行尸走肉,而那些曾闪烁过人类精神最灿烂辉煌光芒的民族,如古希腊,则虽死犹生。这个民族不复存在已近两千年,可是她的体制、她的哲学、她的神话、她的戏剧、她的诗歌、她的雕塑、她的建筑、她的生命的温馨却长留在世界,复活在各个民族的生命中。黑格尔曾经不无悲壮地宣称,“我们首先要排除我们心头那种偏见,以为长久比短促是更优越的事情:永存的高山,并不比很快凋谢的芬芳的蔷薇更优越”①。在我们民族的整个意识中,在我们对人生最高价值的追寻中,仅仅知晓与认可行动本身的社会价值与效应,只要行动及行动目的充满崇高性与悲壮性,那么我们的人生便充满了生存的最高价值和意义,至于在行动的过程中,人的内在生命、个性是否完美、是否深湛、是否丰富,则无足轻重,根本引不起人们的关注。这一代人尽管伟岸,但他们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仍然背负着历史文化的重负,因袭着民族传统生命的构成遗存,而未能获得一个普遍的、超越性的阅读视界,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在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时,其心态、其志向、其襟怀、其眼光,均未能超越民族传统文化所设定的范围与界限。戏剧界的历史发展仅仅是一个表现方面而已。在固有心态模式的拘囿下,戏剧界所能高悬着的标尺与准则,绝对地被圈定在政治一伦理的实用性与直接性之中。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能够激起人们的热情的,只能是那些我们正面临着的各种实际问题与我们正从事着的各种事情。与我们的激情相吻合的,当然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被剔抉、被淘汰,当属意料之中的事了。因为以生、死、爱等为主题的作品,展示人的深层心理,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无异于醉生梦死、颓废堕落。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开放”精神,走向“拒绝阅读”的狭隘现实,固然与特定社会时代的客观环境有关,但不能不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深层心理。
戏剧史上的许多现象,许多争执不下、聚讼纷纭的问题,只有放在整个文化大背景中,才能得到透彻曝光。譬如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多年来为我们所推崇,然而,每当社会出现一次政治上的动荡与转机时,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往往将艺术的僵化之弊归咎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恨不得如弃敝屣般地否定它。对于现实主义的推崇与否定的两种态度,均源于同一种心态和阅读视界。人们没有发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我们的运用中,早已不自觉地被改造变形。那么,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呢?借用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的一句精辟之言,即“不加评判地表现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托多洛夫的这一见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如出一辙。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恩格斯强调指出,“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地把它指点出来”。也就是说,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要求作者不要用自己的阶级倾向、政治信仰、道德信念、哲学观点去刻画人物、影响人物、左右人物,而要让人物自身去说话、自己如实地表现自己。而我们所奉行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恰恰要求在作品中把自己的倾向、爱憎、评价、观点在人物身上传达出来,对于我们的创作目的而言,已经不是什么隐蔽不隐蔽的问题,而是唯恐不能赤裸裸地直白说出来的问题。我们说,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作为一种创作的美学原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托多洛夫等人,均从审美角度来阐述现实主义的精神。他们之所以高度评价与盛赞现实主义,就是由于遵循这条原则,可以冲破作者本人狭隘的党派政治倾向、各种社会见解的拘囿,达到历史与审美的真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