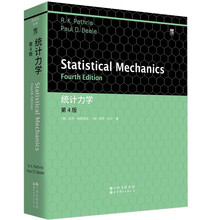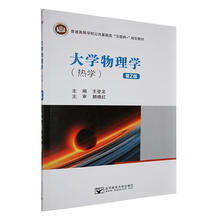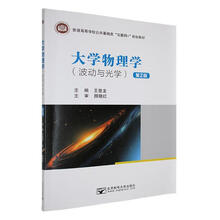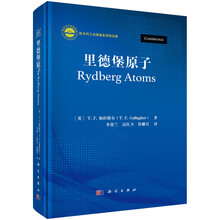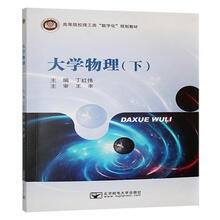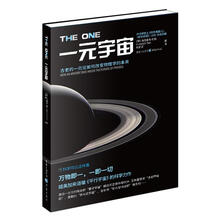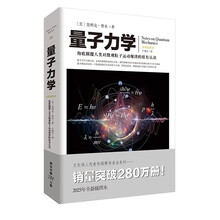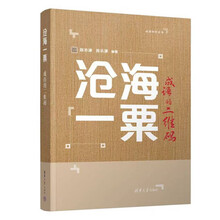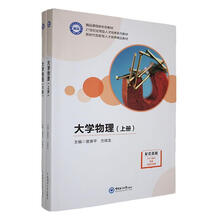第1章绪论
1.1主动流动控制和激励器
1904年,普朗特在德国海德堡举行的第三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了题为“论摩擦力极小的流体运动”的会议报告[1]。这篇短短八页的报告在流体力学发展史上有两个划时代的意义:一是提出了边界层理论;二是开创了流动控制的先河(基于抽吸成功实现圆柱表面流动分离的抑制)。流动控制技术的内涵是通过在流场中引入局部扰动来改变流场的全局特征,使绕流物体在“受力、传热、噪声”等方面朝着有益于控制目标的方向发展。2020年,我国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对流动控制技术而言是个有利的发展机遇。根据国际能源署2020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所有经济领域中,交通运输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23%。通过流动控制技术减少航行器(如民航客机、长途货运汽车、轮船)表面的航行阻力,提高能源动力装置(如叶轮机械、内燃机、航空发动机)的能量效率,能够显著地降低单位里程的能耗、助推双碳目标的实现。
按照引入的扰动是否可控、系统是否需要外界能量注入,流动控制技术可以分为主动流动控制(active flow control)和被动流动控制(passive flow control)两大类[2]。部分飞机机翼/进气道/汽车顶部的涡流发生器及高尔夫球表面的凹坑均是被动流动控制技术的典型代表,这些扰动特征一般基于巡航状态进行优化设计,不具备宽工况下的适应性。相比而言,主动流动控制依靠激励器(吹吸、合成射流等)对流场产生可控扰动。在闭环状态下,扰动的幅值、频率和相位等参数能够根据外界工况的变化进行自动调节,保证始终工作于*佳状态。因此,主动流动控制激励器具有环境适应性强、鲁棒性好、非设计态无附加阻力等优点,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3]。以航空领域为例,欧盟早在2008年就启动了“洁净天空”重大研究计划,参研单位包括欧盟20个国家的几百家单位。该项目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主动流动控制技术实现“减碳、减排、降噪”,使航空运输变得“更便宜、更轻便、更安静”。2014年,“洁净天空”二期重大研究计划启动,规划经费超过40亿欧元。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AIAA)在2010年将主动流动控制技术列为未来美国航空航天领域保持领先的十大前沿技术之一,相关项目得到了美国空军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的持续资助。
主动流动控制技术的激励器多种多样。在理想情况下,为了实现可观的流动控制净收益,激励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频带、能够激发流场中的不稳定模态,从而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借助于不稳定性,靠“蛮力出奇迹”这种思路去改变基准流场特性,往往是得不偿失的[4]。如图1.1所示,国内外研究较多的主动流动控制激励器可以分为三大类:流体类激励器(包括定常射流/吸气、脉冲射流、扫掠射流、合成射流等)、可变固壁边界类激励器(包括振荡丝线、行波壁面、可变形表面等)和等离子体激励器(包括介质阻挡放电、电晕放电、电弧放电和等离子体合成射流等)[3]。
图1.1主动流动控制激励器分类[3]
每种激励器都有其局限性和优点,实际应用中应因地制宜,从结构、激励强度、频响和响应速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以抑制流动分离这一场景为例,吹气类激励器的调控效果十分显著,在典型条件下所需的动量系数(射流动量与主流动量之比)为0.1%~1%[4]。2015年,波音公司联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进行了一次引人瞩目的飞行试验[5]。他们在一架波音757飞机的垂直尾翼上加装了31个扫掠射流激励器,通过抑制大偏转角下的流动分离来增强方向舵的舵效。尽管控制后的侧向力可以增加13%~16%,但加装主动流动控制系统的代价也很高[6]。一方面,扫掠射流激励器从辅助动力装置引走了大量高压空气,影响了其他分系统的使用(如机舱压力调节系统、发动机应急启动系统);另一方面,为了给高压压缩空气降温,专门在机舱外加装了换热系统。这些机械部件(热交换器、管道、阀门等)给整架飞机带来了额外的重量负担,整体得不偿失。
从降低主动控制系统部署成本来讲,零净质量流量的合成射流激励器更有应用前景[7]。从结构上来讲,合成射流激励器仅需要一个封闭的腔体和一个出气孔;通过腔内气体的周期性增压,就能实现射流和吸气流动的轮换交替,无须提供任何气源。腔体增压方式既可以是体积压缩(如压电膜片、活塞和电磁线圈),也可以是快速加温(燃烧)[8]。压电式合成射流激励器的优点是结构简单、工作频率较高(1kHz量级),缺点是峰值射流速度较低(小于60m/s)、可用频带范围较窄[9,10];当偏离谐振点工作时,射流速度会急剧下降。活塞式合成射流激励器可以产生超声速的可压缩射流(600m/s)[11]。但是,受限于机械部件的往复运动特性,其峰值工作频率不超过200Hz。对于燃烧型的合成射流激励器,其射流速度同样可以达到超声速,但受限于反应物的混合和再填充时间,其工作频率不超过100Hz;在结构上,该类激励器还需内嵌点火器和气液管道,整体较为复杂[12]。
1.2等离子体合成射流激励器
1.2.1发展历程
航空中的高速、高雷诺数气流环境(例如,襟翼表面的分离流动、进气道内的激波/边界层干扰)一方面要求激励器具有足够的频带和扰动强度,另一方面还要求结构尽可能简单紧凑[3]。200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Grossman等[13]*次提出采用脉冲电弧放电这一方式对合成射流激励器腔体进行增压。由于常压下的脉冲气体放电具有时间尺度短(μs量级)、能量便于调节的优点,该激励器能够在大于5kHz的高重复频率下产生高速脉冲射流(大于300m/s),是所有合成射流激励器中唯一一个兼具高频和高速两大特征的激励器,航空应用潜力巨大,引起主动流动领域的广泛关注[14,15]。
在过去20年的研究中,国内外曾用不同术语来指代上述依靠脉冲电弧放电进行增压的合成射流激励器,如火花射流激励器[1618]、脉冲等离子体射流激励器[14,19]、等离子体合成射流激励器(plasma synthetic jet actuators,PSJA)[2023]。相比之下,本书认为等离子体合成射流激励器这一术语更为合理,原因主要有两点:*先,火花射流这一术语不准确,在绝大多数研究中所采用的气体放电类型属于电弧放电而非火花放电。火花放电的电流相对较小(0.1~1A量级)、放电维持电压相对较高(1~10kV量级),电离度和温度远远小于电弧。在公开发表文献中,能量沉积阶段所对应的电压多为100V量级,放电电流则高达几十甚至几百安培。此时,等离子体早已处于局部热平衡状态,电离度高、宏观温度高,属于电弧的范畴[14,17,23,24]。其次,脉冲等离子体射流激励器这一术语并没有体现出零净质量流场的特征,很容易与传统脉冲射流激励器及用于医疗的等离子体射流混淆。以前者为例,脉冲射流指代的是对定常射流施加幅值调制之后所形成的非定常射流激励器,不具备吸气特征,需要外接气源。
1.2.2几何结构和放电电路
图1.2为不同类型的等离子体合成射流激励器。一般情况下,激励器由一个陶瓷外壳和一个顶盖组成,它们组装在一起形成一个封闭的腔体。腔体呈圆柱形,其大小取决于放电能量[量级:O(1~1000)mJ],典型的体积为20~2000mm3。腔体的外壳由耐高温且绝缘性能良好的陶瓷材料[如可加工玻璃陶瓷(machineable ceramic,MACOR)、氮化硼等]制成,顶盖既可以是陶瓷也可以是金属件。顶盖上钻有一个或几个直径为0.5~4mm的孔,作为射流出口孔。在陶瓷腔体的底部或侧面,插入若干根钨针,作为阳极、阴极或者触发电极[25]。两电极激励器的阳极兼具触发和注能功能,而三电极激励器将触发和注能功能分离,方便进行能量的*立调节。触发电极和阴极之间的电极间隙一般为1~3mm,保证在10~20kV的高压脉冲作用下能够完成放电击穿。在同一电极间隙下,为了降低激励器的击穿电压,可以利用尖端效应对电极头部进行锐化处理或者在激励器内部涂覆半导体材料。
根据电极几何布局(两电极或三电极)和所需要放电能量的差异,可采用包括高压纳秒脉冲放电[15,27]、电容放电[25]、电感放电[24]和脉冲直流放电[28]在内的不同放电电路完成激励器腔内气体的增压过程。图1.3为用于三电极等离子体合成射流激励器的典型电容放电电路。该电路使用直流电源(典型电压:0.5~3kV)对储能电容器C1进行充电,峰值充电电流与限流电阻R1相关(典型阻值:100~1000Ω)。由于直流电源峰值电压通常低于电极间隙的击穿电压,因此,还需要额外的高压脉冲电源进行放电触发。当高压触发脉冲作用在触发电极和阴极之间的气体间隙上,两者之间形成微弱的火花放电、建立起导电的等离子体通道。一旦该通道形成,阳极和阴极之间的击穿电压大幅度地降低,储存在电容器C1中的能量以脉冲电弧加热的形式迅速释放到电极间隙中。当电容储能释放完毕后,电弧通道熄灭,电容器再次由直流电源充电,等待下一个触发脉冲。为了隔离低压充电回路、保护高压触发电源,在电容C1和阳极之间还增加了一个高压二极管D1(非必须)。由以上原理描述可知,脉冲放电的放电能量与直流源的初始电压和电容器C1的容值相关,而放电频率则由触发频率决定。
图1.3用于三电极等离子体合成射流激励器的典型电容放电电路
法国宇航院[24]、国防科技大学[29]和空**程大学[22]在上述电路拓扑基础上提出了多种改进设计。在Belinger等[24]的研究中,电容器直接由高压变压器充电,其峰值电压足以能够击穿电极之间的气体间隙。因此,放电电路无须额外的高压触发电源,极大地简化了拓扑结构。但是,去掉*立的触发电源以后,脉冲放电能量由击穿电压决定,而击穿电压又很容易受到电极距离、电极尖端腐蚀和腔体密度的影响。这种多因素的交织耦合给等离子体合成射流激励特性的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在Wang等[29]的研究中,由于高压触发电源自带保护电路,因此,可以去掉隔离二极管D1;通过放电电流在电路中的周期性振荡和多次注能来提高放电效率。Zong等[22]用磁开关取代了高压二极管,并将触发功能集成到阳极,在保证放电能量和频率能够*立调节的前提下减少了激励器的电极数目。
1.2.3工作原理
如图1.4所示,PSJA的一个完整工作周期包括三个阶段:能量沉积阶段、射流阶段和吸气恢复阶段。在能量沉积阶段,外部电路在电极之间产生强烈的脉冲电弧放电,迅速对腔体进行加热增压[时间尺度:O(10μs)]。由于电弧加热区域局限于电极间隙附近,因此腔内温度和压力的分布极其不均匀。这种空间压力的突变会产生超声速的冲击波,自放电加热区域向其他未加热区域传播。腔体的增压过程实际上就是靠冲击波的传播和反射来实现的。在射流阶段,受腔体内外压差驱动,高温、低密度气体通过出口喉道排到外界环境,形成高速喷气流动。射流脱离出口后,会自然卷成一个启动涡环。随着腔内气体的不断喷出,腔内压力单调下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喉道内气体的惯性,射流速度为零时喉道两端的压差并不为零,而是一个负值。该负向压差才是激励器吸气恢复的真正驱动力,而并非早期研究中部分国外学者所提出的内外热交换。在吸气恢复阶段,外界高密度、低温气体被吸入激励器,与腔体内部残留的高温、低密度气体混合,从而使激励器恢复到初始状态。这种射流和吸气的交织作用,会在出口附近形成一个鞍点[7]。
图1.4一个周期的三个工作阶段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节主要从激励特性和流动控制应用两个方面简要回顾国内外的研究概况。激励特性研究的目的是获得各类参数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