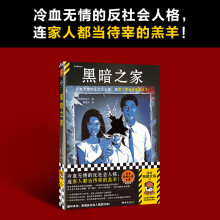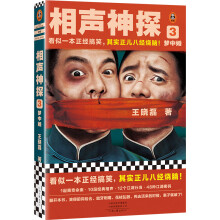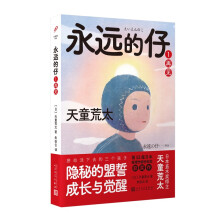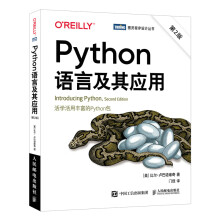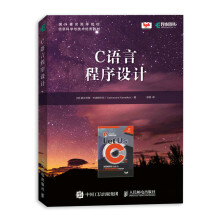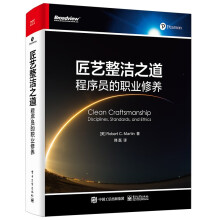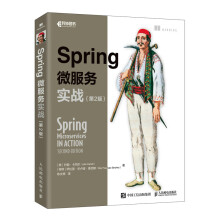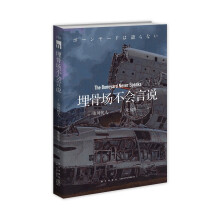第1章新型电力系统中电化学储能的角色
1.1概述
能源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人类社会的进步一直依赖于越来越多的和越来越集中的能源形式的转换。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进程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对更大能量存储和能量流向的控制。在能源技术的进步之下,人类的城市规模逐渐扩大,人口数量也得到增长。如果没有能源开发和使用方面的创新、技术能力的增长和对周围世界更深入的了解,以及确保更好的生活质量的努力,人类都不会如此迅速地进步。
在过去的200年里,人类获取能源的方式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图11所示。在迈入新能源时代以前,人类的能源技术主要有四个历史节点。在1800年以前,人类的能源开发主要依靠焚烧自然生物以获取热能;到185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次实现了石油的商业化开采;1930年后,随着蒸汽发电和燃煤发电厂的发展,煤炭用量开始增加;1960年后,随着内燃机汽车技术的突飞猛进,石油需求量激增,到1970年已占全球能源消耗的40%。总体上,从能源技术水平来说人类目前已经历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目前正以强劲的势头向新能源时代迈进。在近200年的能源技术变革和能源结构的转型中,化石能源已被人类充分开发利用,但也带来了一定副作用。由于化石燃料的大量利用、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天气和极端气候的上升几乎已经达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人类逐渐意识到需要对此做出改变。随着《巴黎协定》的签订,全世界希望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希望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国际可再生能源的世界能源转型展望描绘了一条不断发展的道路,以实现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气候安全的未来。其1.5℃路径为加速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路线图,将电气化和效率作为变革的关键驱动力,并以可再生能源、氢气和可持续生物质为支撑。然而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同时也指出,虽然能源转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也有益,但它是不会自行发生的。世界各国需要自主采取行动制定符合国情的策略,引导全球能源体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图11能源发展历程来源: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世界上人口*多的国家、*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大的碳排放国家,可以说中国低碳能源转型的成功实现将是《巴黎协定》中抑制全球变暖目标实现的重要一环[1]。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IRENA)、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对我国温升2.0℃和1.5℃情境下能源转型的路径进行了探索[2]: 在温升2.0℃和1.5℃的目标下,能源消费情景和能源供应结构将发生极大变化,电力消费量将被推上高峰,低碳能源的需求量将随之剧增。按照当前经济和能源的发展政策推演,2050年我国电力需求将达到10.7万亿~11.6万亿kW h[3]。而在2.0℃和1.5℃的目标下,2050年我国电力需求将分别增长到11.75万亿~12.5万亿kW h和14.5万亿~15万亿kW h[4,5]。面对急速增长的电力能源需求,2020年我国提出了在2030年达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为此,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在《美丽中国2050年—中国能源经济生态系统》报告中指出,我国在向2050年清洁高效能源系统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分为三大块: **是在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下,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将大幅下降,伴随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建筑部门和交通部门的能源消耗将大幅上涨,而在低于2.0℃的场景中,更多的电动汽车将被引入,交通部门能源消耗将进一步增长;第二是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化石能源将很大程度上被电力取代,电气化将是提高2050年总体能源使用效率中*关键的一环;第三是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的支柱性电力来源,在现有政策规划的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的占比将达到36%,若是在2.0℃的场景中,这一数字将达到54%。同时,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指出为实现“美丽中国”和全球2℃的温升控制目标,2020年以后我国新增发电装机应以风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为主,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应达到92%。因此,加快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1.2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及其特点
受资源禀赋约束,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集中于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根据IRENA统计的数据,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及发电量如图12所示。从装机量来看,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水力发电的开发已逐渐趋于平缓,年增长装机量基本维持在10GW/年左右;而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得到大力发展,截至2021年,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装机量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中的占比均已达到30%以上。但从发电量来看,目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仍由水力发电主导,由IRENA在2019年的统计数据可见,水力发电量占比达到64%,而风力发电量和光伏发电量的占比仅为21%和11%。在“双碳”目标下,预计到2060年中国96%的装机量和发电量由可再生能源承担,其中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占比之和须超过80%,发电量占比之和须超过70%[6]。
图12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及发电量
以可再生能源的渗透率,即全年度下可再生能源机组可输出总电量与总负荷需求的比例为评估指标,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中比例渗透阶段、高比例渗透阶段以及极高比例渗透阶段。中比例渗透阶段下,可再生能源的渗透率为10%~30%,风电及光伏装机主要集中于风光资源丰富区,对负荷中心的远距离送电和集中式并网是当前阶段的主要挑战。高比例渗透阶段下,可再生能源的渗透率为30%~50%,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的增长,并网方式将从中比例阶段下的风光资源丰富区局部并网转向多地区的集中式和分布式并网,风电、光伏的不确定性将对电网的可靠性产生显著影响。极高比例渗透阶段下,可再生能源的渗透率为50%~100%,可再生能源将以风电和光伏为主,多种能源形式之间的联动、互补及协调发展稳定、可靠至关重要。
截至2019年,中国有六个省区的可再生渗透率(风电、光伏)超过了20%,但全国范围内的渗透率仅为8.6%,远低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发达的欧洲国家(丹麦为45%,德国为27%)。此外,中国目前可再生能源装机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随着政策推移,可再生能源布局将持续向中部和东部地区转移。
与传统发电机组使用煤炭、水力等资源不同,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极度依赖于自然环境的风能和太阳能,这类资源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特点,导致电源间歇式波动随机率达0%~100%。可再生能源机组在发电方式、控制手段、并网需求及外部特性等方面同样与传统机组存在区别,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的增加将导致电力系统特性及机理发生本质的变化。
1.电力电量平衡
传统电力系统中,负荷的随机波动平衡问题主要由控制常规机组来解决。当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在电力系统中的比例提升后,其将承担一定的负荷平衡的责任,然而可再生能源的出力具有不确定性。在无风天气下,风电出力将大幅下降,而在阴天及夜间时,光伏发电量也无法维持高水平。这导致可再生能源机组的出力与用电负荷*线不匹配较为严重,传统机组的调节负担增加。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进一步升高,电力平衡难度增加,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存在一定隐患。
2.发电量消纳
中国的风、光资源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高原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资源丰富地区受经济发展约束,电力需求相比于经济发达的中部、东部地区较为不足,同时受限于电力外送能力,很大一部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无法消纳,将造成严重的“弃风弃光”现象。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