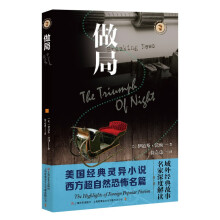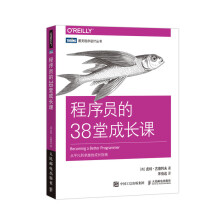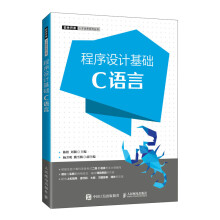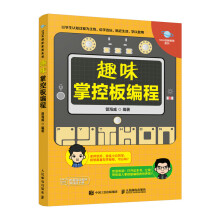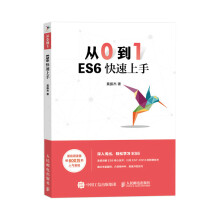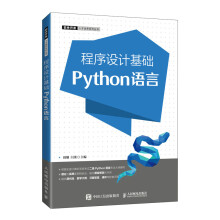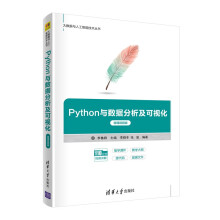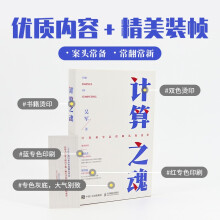《灾后社会日常生活空间的地方型塑:以北川新县城为例》由绪论、正文、结论及参考文献等部分组成。
第一章“绪论”,从说明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开始,对“空间”“地方”相关概念及两者的关系进行梳理和讨论;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论述日常生活视角于“地方”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本研究在学术层面的突破;对相关研究方法以及田野点的选择等进行说明。
第二章“北川县城的历史地理沿革和城镇空间图景”,通过追溯北川老县城空间形成的历史,探讨老县城为当地人提供的身份归属和情感维系价值。而2008年的特大地震在摧毁北川老县城物理空间的同时,也摧毁了当地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空间,为北川人的未来生活带来无数不确定性。
第三章“被‘赠予’的城镇空间:新县城的规划和重建”,对震后北川重建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北川新县城的自然地理环境、区位格局、城镇面貌均实现“升级”,与老县城产生强烈对比。源于国家权力和专家系统的话语和要求对新县城未来发展进行框定,并间接对城镇空间秩序和生活秩序提出更高要求,从而使空间商榷和文化调适成为北川人未来生活的重要主题,也意味着失去“地方”(家园)的北川人面临“地方”(家园)再造的问题。
第四章“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占道菜场’空间的生成与演变”,围绕新县城一处“占道菜场”展开讨论,对“占道菜场”的去留问题如何逐渐成为各方角力的焦点进行解释,指出“占道菜场”与地方传统集市相仿,其方位及其所带有的人气、热闹等特质,贴合北川人关于集市的记忆、认知和想象,而这种特质是政府规划中的公共菜场所不具备的。“占道菜场”作为灾后社会情感世界的依托,长期以合理不合规的状态存在于北川人的日常生活中,富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新的“地方”正由此产生。
第五章“抗震纪念园的空间规划、意象及使用争议”,呈现的是灾后公共纪念空间——抗震纪念园的规划过程、使用情况及意象争议。新县城建成并移交北川后,抗震纪念园迅速转型为市民公园和地方文旅空间,难以发挥灾害纪念、慰藉灾民等价值。中国政府是灾害纪念空间建设中的绝对主体,其建设物质性的纪念空间的行动背后,也将展示抗灾、救灾和重建等阶段的成就作为空间营造重心。地方政府作为实际管理方,往往会根据地方综合发展需要,来调整灾害纪念空间的使用策略,而抗震纪念园转型为公共休闲空间,更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园区纪念性价值从而被进一步淡化。灾后特定的社会心态维护且发展了重建空间的道德秩序,北川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支持抗震纪念园日常性建构的力量。为满足社会祭奠需求,开辟于县城偏僻处的多处违规祭祀空间则属于北川政府与北川人相互妥协下的产物。
第六章“广场空间的舞蹈实践与‘地方’社区秩序的生成”,主要围绕北川人学习羌族舞蹈萨朗并由此建立有关“社区”的地方感展开论述。地震后,萨朗舞成为国家向灾后重建空间中“注入”的标志性羌族文化。随之而来的是,北川人“真假羌族”以及萨朗舞真伪等问题长期在北川社会发酵。但在地方政府有意开展的社区舞蹈日常教习实践中,北川人眼中的萨朗舞逐渐不止于舞蹈本身,它还是培育地方社区归属感和维系社区秩序的“中介”。通过萨朗舞日常教习活动,社区广场也成为新县城安置社区中新的公共活动中心和社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空间,使社区真正成为人们确认自我身份归属的重要纽带。
第七章“总结与讨论”,具体分析北川人“地方感”生成的主要维度,指出灾后社会“地方-空间”关系的特殊之处。从北川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地方-空间”未能避免紧张关系,“地方感”的维系理应成为城镇规划设计时应考虑的面向。研究认为,需以微观视角正视和理解灾后重建社会的“地方-空间紧张”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掘空间之上“地方”存续的价值,从而弥补权力、资本层面空间生产的种种不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