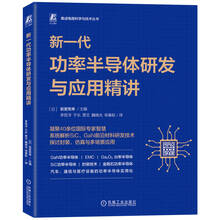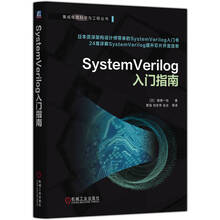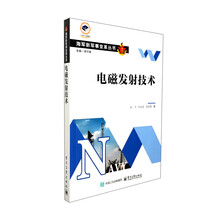第1章 绪论
1.1 风力发电发展概况
风能是一种储量丰富而且安全清洁的新能源,围绕“绿色低碳转型”理念,我国正大力推动风能等新能源的高质量发展,大规模开发利用风电已成为我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优化能源结构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显示,风电装机容量预计于2050年达到24亿kW,届时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五成以上,新能源将从补充性能源演变为替代性能源[1]。与陆上风电相比,海上风电具有资源条件稳定、就近消纳、风电效率高等优势。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海岸线,可开发利用的海上风能达到了5亿~7.5亿kW,远高于陆上风能的2.53亿kW。其中,近海风能开发潜力约为2亿kW,远海风能开发潜力约为5亿kW。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515.7万kW,约占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的54%。截至2022年底,中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3051万kW,占全球海上风电装机总容量的44%,保持****地位。图1.1所示为2016~2022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统计结果。
图1.12016~2022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
注:1G=109
然而,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仍然以高碳的化石能源为主,占比约为85%。为推动能源生产低碳化与消费端电气化的转型,加大新能源开发力度是必然趋势。风力发电作为目前新能源利用中技术*成熟、*具规模开发条件、发展前景*看好的发电方式,已成为可再生能源的第二大主力[1],如图1.2所示。
图1.2 可再生能源供应量发展趋势
*tce(ton of standard coal equivalent),能源衡量单位,即吨标准煤当量
1.2 风电变流器发展及面临挑战
大功率并网风力发电机组(以下简称风电机组)及风电场的安全可靠运行将对提高电网稳定性、实现负荷合理分配以及降低发电成本产生重要影响[2-4]。风电变流器是风电并网装备的核心,是实现风电机组电能回馈至电网的关键控制通道,是直接影响大功率风电机组及入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环节[5-7]。风电变流器基础核心部件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IGBT),其可靠性对变流器及风力发电整机的可靠性至关重要。通过对变流器可靠性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知,在各类失效因素中,约55%的失效是由温度及其应力循环因素诱发[8],如图1.3所示。由于风能固有的间歇性特征,风电机组会出现长时间、频繁和大范围的随机出力变化,其电能转换单元将持续承受剧烈的热应力冲击,使变流装置在风电并网运行中的可靠性变得极其脆弱。大功率风电机组设备故障在机组停机原因中占比高达65%~75%,并产生30%~35%的运维成本[9-10]。风电变流器、电控系统等电气关键部件的高故障率[11-12],严重阻碍了高效、高可靠风力发电技术的发展,如图1.4(a)所示。由于变流器功率器件内部器件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差异,变流器功率器件持续承受交变电热应力,其在变流器各元件故障率中占比*高,达34%,如图1.4(b)所示,严重降低了风电变流器的运行可靠性。
图1.3 影响变流器可靠性的应力源 图1.4 风电机组与变流器各元件故障率
此外,风力发电系统装备在户外受气候环境影响较大,加速了材料和内部封装结构的老化[13,14]。IGBT器件失效前所经历的循环周期数由结温波动幅值、*高结温、平均结温、*低外壳温度及器件周期导通时间等因素共同决定[15]。IGBT器件典型结温波动幅值与失效周期寿命变化*线[16]如图1.5所示。
图1.5 IGBT器件失效周期数与结温波动幅值的关系*线
由图1.5可知,随着结温波动幅值的增加,IGBT器件的失效周期数将急剧减小;在结温*大值为150℃,结温波动幅值为40℃的情况下,失效周期数为1.7×106次。因此,若结温波动频率为8Hz,则IGBT器件运行能力仅为2.5天左右。由此可知IGBT器件内部器件结温变化,是影响其疲劳寿命的关键。
目前市场上兆瓦级以上的风机应用广泛,所需功率器件等级也达到数千安,为了提高变流器可靠性和减小成本,普遍采用芯片并联和功率器件并联来提高电流等级,这就对并联均流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并联器件间线路杂散参数与驱动触发信号不一致均会引起电流不平衡[17],而且双馈风电机组机侧变流器长期在较低的输出频率下运行,进而导致同一变流器内不同功率器件间或者同一器件内不同芯片间温度存在差异,并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形成热薄弱环节。这使得功率器件实际使用寿命大大缩短,以及机侧变流器的故障率增加,且远高于网侧变流器,不利于风电机组长期稳定运行。
此外,虽然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逐年增高,发展速度较快,但受限于风能资源与电力负荷中心的逆向分布,我国普遍采用大规模风电“集中式开发、远距离输送”的运营模式,因此风电场多建在电网较为薄弱的偏远地区,使得风电机组所连电网实质上是一个存在电压跌落、电压不平衡、谐波畸变等各种形式故障的“弱电网”。双馈发电机(double fed induction generator,DFIG)定子直接与电网相连,电网电压跌落时产生的电能将不能全部送出,定转子感应出的过电流和过电压将导致变换器、绕组绝缘以及直流母线电容的损坏[18]。为满足现代电网规范要求,实现电网在故障下不脱网或故障穿越要求,国内外研究多从保护或提高电网电气性能的角度出发,采用改进控制策略和增加额外硬件保护的方法实现故障穿越。但不同的控制策略同样会对变流器IGBT和换流二极管的结温大小和波动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变流器系统的可靠性[19-22]。
总之,风电机组由于运行工况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风电变流器IGBT不仅受机组运行工况长时间尺度应力影响,而且受变流器开关频率短时间尺度应力作用,因此风电变流器IGBT器件内部应力建模与特性获取困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风电变流器IGBT器件运行可靠性具有挑战性。因此,开展风电变流器IGBT器件内部应力特性分析及主动热调控方法研究,进一步掌握风电变流器功率器件内部的结温计算方法及分布规律,获取其老化失效寿命,提升IGBT器件运行可靠性,对风电变流器安全稳定运行及风电主动支撑电网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3 IGBT器件应力特性及热管理研究现状
1.3.1 IGBT应力分析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IGBT器件结温计算方法的研究,可大致分成物理接触法、光学法、温敏参数法、热网络法等四种。
(1)物理接触法是将热敏电阻或热电偶直接接触IGBT器件的硅芯片(简称IGBT芯片)表面来测量其结温。物理接触法可以直接测量芯片结温,但是需要附加测量设备进行接触测量,易受封装材料(如硅胶)干扰,同时需改变封装结构或直接将器件开封,且功率器件内部空间有限。
(2)光学法利用反射光子的能量与照射温度的对应关系推测结温,具有测量准确、空间分辨率高、可实现实时测量等优点[16-17]。其中,红外摄像法测量IGBT结温是*常用的光学测温技术,文献[17]利用高速红外测温设备对IGBT芯片的结温进行了实时测量。红外摄像法是一种非接触式测量方法,能迅速反映结温变化,能从多点测量中反映芯片表面的二维温度分布。但是和其他光学测温方法一样,红外摄像法不适用于全封装器件,只适合在实验室研究已开封的器件,而且整套设备价格昂贵。
(3)温敏参数法是利用功率器件的一些电学参数受温度影响明显且具有线性特性的特征,建立其二者之间的联系。该方法只需测量IGBT器件外部电参量,不需要改变器件的封装结构,测量相对简单,文献[18]~[20]建立了饱和压降Vce等热敏参数与IGBT芯片结温之间的关系*线,对结温进行间接测量。然而,这类测量方法需要在通以小电流的情况下进行,而IGBT器件实际运行时如果关断后再通以小电流测试,会对IGBT器件以及由其构成的电路系统造成干扰。因此,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结温的在线测量,只适合实验室阶段的研究。
从上述三种方法的分析可知,虽然实验测量方式的准确性较高,但是由于IGBT器件的密闭封装特性,该类方法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此外,诸如红外成像仪等设备的较高成本以及较复杂的实验条件也制约了实验测温法的广泛应用。因此,变流器功率器件的结温仿真预测方法就成了其整体设计、器件选型以及系统运行可靠性评估的重要手段。
(4)热网络法基于集中参数的功率器件电热耦合模型,利用器件损耗参数及运行参数,通过其电损耗模型和热网络模型来实时计算功率器件的结温及其变化趋势[21-23]。图1.6为逆变器功率器件结温测量的电热耦合模型法的结构框图。
针对电热耦合模型法测量IGBT器件的结温,已有部分文献进行了相关研究。文献[24]、[25]基于开关周期的损耗分析方法,研究了IGBT器件的损耗及结温计算模型;文献[23]采用集总参数法,基于器件的瞬态热阻抗参数,建立了RC(即电阻和电容,resistance-capacitance)热网络结温计算模型;文献[26]提出一个实时结温预测模型用以实现功率器件的健康管理;文献[27]采用热网络模型分析了不同的散热方式对变流器IGBT器件结温的影响。由于功率器件多芯片热源间存在热耦合影响,如果仅采用当前现有的电热耦合模型来计算大功率变流器多芯片并联功率器件的结温,结温测量可能不准确。
图1.6 结温测量的电热耦合模型法
RG为热阻;Tj为结温均值;I、U、D分别为逆变器输入电流、端电压和占空比;FWD为续流二极管;
PT、PD分别为IGBT、FWD损耗功率;TTj、TDj分别为IGBT和FWD的结温
焊层疲劳被认为是导致功率器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28-33]。IGBT器件各层材料的线性热膨胀系数不同,工作过程中温度的波动会使各层材料承受交变应力,导致IGBT硅芯片与敷铜陶瓷板(direct bond copper,DBC)上铜层以及DBC下铜层与铜基板之间的焊层产生裂纹,如图1.7所示。裂纹在温度波动持续冲击下逐渐延展,*终造成IGBT内部芯片、焊料层、陶瓷层等各层材料的分层脱落;由于各层间有效接触面积减少,热阻增大,促使温度升高,又进一步加快功率器件的老化失效。焊层疲劳导致的功率器件老化对结温计算的影响问题,一直是变流器可靠性研究的热点。
图1.7 功率器件焊层失效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功率器件的结温计算和疲劳老化的研究工作已有部分成果。文献[34]对比研究了电流迟滞控制、正弦脉宽调制(sinusoidal pulse width modulation,SPWM)、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pace vector pulse width modulation,SVPWM)三种调制方式下脉冲负载对功率器件结温的不同影响;文献[35]以近海风场永磁同步电机为研究对象,利用Foster(福斯特)热网络分析了机侧、网侧IGBT器件的结温特性;文献[13]考虑多芯片热源之间的耦合作用对IGBT器件功率循环能力的影响,对不同的结温计算模型进行了误差分析;文献[14]、[15]研究了基于壳温的风电变流器状态监测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器件疲劳老化对结温计算的影响。但是上述文献都是基于IGBT器件热阻为固定值的假设,无法追踪结温在器件不同寿命时期的演变历程,且不同风速下功率器件内部不同的焊层疲劳老化程度与器件结壳热阻变化的关系尚未研究。文献[36]利用不同功率循环次数下结温的变化量来进行功率器件的状态监测,但其对疲劳寿命后期结温的评估仍是基于热阻固定的常规热网络模型;文献[37]从热传导路径的角度分析了功率器件的结温计算,但是其仅仅考虑基板焊层老化引起的导热路径变化,而没有考虑老化影响可能更为显著的芯片焊层疲劳。此外,文献[38]~[43]分别从不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