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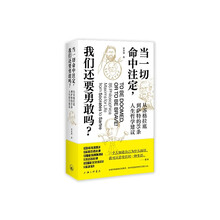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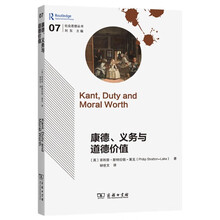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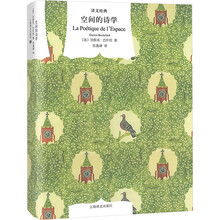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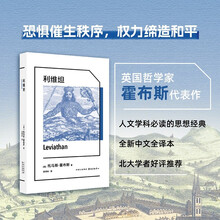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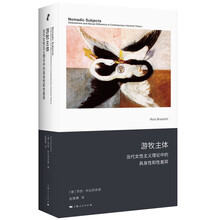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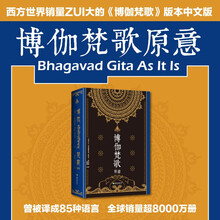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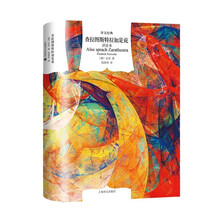

1.历史与当代思潮的对话,生命政治研究的前沿成果。本书以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与人之存在的关系的论述为起点,通过思想史与当代思潮的对话的双重路径,探讨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之下,政治与技术的交汇所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将当代的生命政治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2.重读经典哲学理论,呼唤一种更积极的生命政治。本书批判了海德格尔的理论和受其影响的一系列当代哲学理论中所蕴含的死亡政治,并且通过对福柯、弗洛伊德、德勒兹等人的经典理论的重新阐释,提出和倡导一种更为积极的生命政治。
3.带领读者认识后人学理论,启发人们对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反思。“后人学译丛”聚焦于人与非人的界限、生命与后人类、后人类的技术进化等问题。本书为“后人学译丛”之一种,从对现代生命政治中“死亡”主题的反思切入,启发读者对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反思。
4.专业译者精心翻译,译作精准切当、行文流畅。本书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精心译成,不仅忠于原著,对原著所涉及的西方哲学理论及术语进行了精准的翻译,而且行文流畅,保持原作者行文风格的同时,帮助读者跨越语言的藩篱,与原作进行深入的交流。
编辑推荐
今天的生命政治是否在从事着新自由主义的工作,对具体的威胁毫不关心,而只聚焦于物种层面的生死问题?我们当下对于生命政治的理解,是否过分依赖于死亡这一悲剧性主题?——这是提摩太·C.坎贝尔在《生命的尺度》开篇中发出的诘问。随后他说道,恰恰在技术问题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死亡在生命政治思考中占据了上风。如此,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关于技艺的难题,使得有关生命政治的讨论不断地走向死亡的视角?于是,他以此为突破口,以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与人之关系的论述为逻辑起点,探讨现代的政治和技术所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并试图找到一种办法,来超越这种异化,实现对人真正生命的救赎。
在本书当中,坎贝尔先是对海德格尔的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批判,在其理论著作中解读出了正当的写作与不正当的写作,并由此延伸出正当的生命和不正当的生命。然后,作者对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哲学家的生命政治理论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反思,指出阿甘本有意将“装置”这个词与海德格尔所说的不正当写作的观念并置,埃斯波西托则试图思考一种非人格的生命可能性。作者还花费了较多的笔墨来分析斯洛特戴克等哲学家的理论和批评,他们与阿甘本等人一起探索着生命中的死亡路径。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提出了一种注意力和游玩中的生命实践,来避免让技艺陷入死亡的困境,从而将生命政治引入更积极的方向。
坎贝尔的整部著作都跃动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其展开分析的路径清晰合理,结论亦是鲜明有力。相信这本书会成为广大读者了解现代生命政治、了解生命的有益参考。
生命政治是否已然成为一个痴迷于死亡的研究领域?本书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生命政治理论,它以海德格尔对技术与人之关系的论述为起点,通过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想的对话,来探讨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之下,政治与技术的交汇所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以及超越这种异化的可能性。
作者首先通过聚焦海德格尔的经典理论,探讨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及其对人的存在的遮蔽;而后以福柯的规训和人口理论为中介,分析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所说的例外状态、赤裸生命,以及他们的死亡政治理论。最后,作者提出,在技术变革的时代,只有重新建构人与技术的关系,才能实现对人的真正生命的救赎。本书问题意识强烈,论述清晰有力,将为读者了解生命政治、了解生命提供有益的参考。
《神圣人》和《奥斯维辛的残余》中的拯救权力
有点意外的是,也正是这里代表了阿甘本与海德格尔本体论中隐含的死亡政治学分道扬镳,阿甘本多次将海德格尔的拯救权力消极地理解为福柯意义上的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权力。我们可以在《奥斯维辛的残余》中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那本书中,阿甘本的死亡政治观与早期的《神圣人》有所重合。在《奥斯维辛的残余》中,阿甘本从普莱莫·列维(Primo Levi)、哈维尔·比沙(Xavier Bichat)和福柯的一系列作品中得出了这个观点。这些最重要的段落实际上是通过生命权力来思考生命技术的小谱系学,阿甘本认为这就是“生命体和言说的存在者之间、zoē和bíos之间、非人和人之间的绝对分离”。福柯对生命权力和主权权力的思考启发了阿甘本的反思:
我们已经看到,福柯通过两个互文的对称表达,阐明了现代生命权力和古代领土国家的主权权力之间的区别。使其死,让其活,概括的是主权权力的程序,即权力首先是杀死人的权利;相反,使其活,让其死,是生命权力的标志,其主要目的是将对生命和生物性的关怀转变成对国家权力的关注。根据之前的思考,在这两个表达之间也暗藏着第三个表达,这个表达阐明了二十世纪生命政治最明显的特征:不再是让其死或让其活,而是让其活着。20
且不论阿甘本对福柯的解读是否标志着生命政治的观念的奇思妙论(他毫不含糊地省略了出现在十八世纪末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生命政治),阿甘本给出了一个立场,即技术与不可避免地导致生命只能活着的主体化和去主体化的过程有关。所产生的“主体”不过是一个外壳,他并不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活着。阿甘本在许多地方都表现出与海德格尔本体论的重合,尤其在他将可能性、不可能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当作“本体论的操作因子”时,认为“在每一次涉及人与非人、‘使其生’或‘让其死’的抉择时,为了存在而进行的生命政治斗争使用了毁灭性武器”。这种毁灭带来了海德格尔在《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的其他灾难,如语言的灾难,语言延伸和消解了伦理和道德的责任,这种灾难源于语言本身的威胁。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的灾难也威胁着生存,其根源就是语言沦为“沿着物化的路径(一切事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致的、可以触及的)加速传播的牺牲品,在这条路径上,一切事物都分散开来,无视一切限制”。这样,语言为公共专制王国所统治,它进一步决定可以认识什么,什么事物被拒斥为不可认识的东西”。与《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不同,在《奥斯维辛的残余》中,阿甘本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传播效果的担忧,转化为一种专属于某个特权团体的政治生命(bíos),以及那些只能苟延残喘活着的zoē。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区分bíos和zoē的重要性更加显著。在关塔那摩基地(Guantánamo)和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虐囚事件的细节被揭露之后,呈现出来的恰恰是生命政治体系的特征,显然其特征就是让生命只能活着。如果关塔那摩基地被永久关闭,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归功于吉奥乔·阿甘本的思想。话虽如此,如果我们仅仅认为阿甘本只是在针对反恐战争进行生命政治批判,那么我们就理解不了阿甘本分析中的激进主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仅仅将阿甘本的洞见局限于恐怖分子的生命政治的生活(或生命),那么我们就削弱了阿甘本观点的价值和意义。当阿甘本谈到为了存在而进行生命政治斗争时,他有意无意地提到了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由于技术的地位日益提高,人与存在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从而产生了这种威胁。阿甘本通过福柯以及他对阐述和生存之间关系的判断继续前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注意到,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残余》末尾得出的结论(或者说他留下的坑),恰恰就是海德格尔谈到的传播与不正当写作之间的关联。所以,福柯的说法是“阐述并非由实在确定的事物,并不具有明确的属性,相反,它是一个纯实存,即某种存在物(语言)发生的事实”,这段话具有福柯考古学式的效果,仿佛这就是不正当写作的海德格尔式要素:“考古学仅仅占据这些命题和话语作为自己的领域,也就是说,占据语言的外部、语言实存的野性事实。”当阿甘本谈到某种存在物的实存或它与语言的关联时,他重新激活和建构了海德格尔本体论中的正当和不正当的原初区分。
不过,海德格尔不断地画出一道区分线,区分了哪些是可以得到拯救的存在者,由于存在尚未完全消失,从而可以标示出布尔什维克或动物的名称以示区别,阿甘本却是在主体自身内部画出了这道区分线,的确,现代主体见证了它自己的去主体化,这就是西方历史之人与列宁主义的形而上学之人重叠的结果。阐述和语言在既有的“存在物”之上留下了痕迹,作者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看着它在多大程度上沦为废墟。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注意到,当阿甘本最后完成对福柯的解读时—用考古学来说明区分主体的前提,一种是穆斯林,即“活着的存在者”;另一种是见证者,即“言说的存在者”,他最终将海德格尔的正当和不正当的区分推向极致,现在几乎不知道区分和分离生命的内在边界。在《奥斯维辛的残余》的结尾,阿甘本通过解读圣保罗的《罗马书》中的“剩余”,重新概括了海德格尔的拯救权力,后来,在《剩余的时间》中,他也没有改变这个看法,即剩余的观念无法处理不正当性对正当性的冲击,语言痕迹就像地震仪一样,记录了二十世纪生命政治的灾难。
当然,阿甘本知道海德格尔的正当和不正当的本体论对他的影响。事实上,在《穆斯林》这一章中,阿甘本和海德格尔一样,引用了荷尔德林的原则,“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他悖谬地将集中营解读为这样的场所,即在那里,“在正当和不正当、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所有区分,彻底消失了”。他继续说道:“在这里,按照这个主要原则,正当性的唯一内容就是不正当性,而这一原则恰恰是反过来证明的,即不正当性的唯一内容就是正当性。”将不正当之人当作单独的阵营分离开来,与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在那时的做法一样,那时,“生命政治直接与死亡政治完美重合”。阿甘本早先在《无目的的手段》中重新概括了正当和不正当的关系,
那时,他讨论了在人民和人口之间的生命政治区分中感受到的区分另一种正当和不正当的因素,认为其“将本质上的政治身体变成了本质上的生物身体,生与死、健康与疾病,都必须受到管制”。对阿甘本而言,集中营命名了这样一个空间,即在其中人民变成了人口,人口进一步变成了赤裸生命。这部分是由于在阿甘本的解读中,死亡权力十分重要,这恰恰是因为阿甘本不仅将拯救权力(在《无目的的手段》中,他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的社会”或《奥斯维辛的残余》中的“弥赛亚王国”)用于集中营本身,而且用于所有的当代生活形式。在《无目的的手段》中,我们看得最清楚,在那些段落中,阿甘本解构了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不过是两极之间的辩证运动:“一方面,人民是一个整体,是政体的总体;另一方面,人民是一个子集,是所需的和被排斥的碎片化的多元性集合。”阿甘本认为,正是这种赤裸生命和政治生命的基本区分,在现代死亡政治的阴影下构建了当代政治。
“后人学译丛”总序 i
序言:在死亡和技艺之间的生命 i
第一章 正当的区分:海德格尔、技术和生命政治 1
技术和手的正当性 5
生命与写作条陈 20
奥秘、技术、邻近性 28
《人道主义的书信》:生命政治学 38
死亡的邻近性:今天的不正当的写作 46
第二章 死亡政治的装置:不正当写作和生命 51
生命的词汇 53
即将来临的共同体的不正当方式 56
《神圣人》和《奥斯维辛的残余》中的拯救权力 61
跨越诸时代的《神圣人》 71
处置生命 73
自由主义的死亡政治学 80
抵抗死亡政治的装置 83
区分生命,漂向死亡 87
灾难预告 90
死亡政治学和废弃的誓言 95
肯定装置 102
死亡,它自己的旋律 126
第三章 赤裸呼吸:斯洛特戴克的免疫生命政治 129
全球化的死亡空间 132
免疫体的恐惧 148
作为赤裸呼吸生命的zoē 153
现代先锋派的非人性 157
愤怒的死亡政治学 162
生物技术的死亡政治学(一):福柯与斯洛特戴克 171
生物技术的死亡政治学(二):全球化的基因库 175
第四章 bíos的实践:作为技艺的注意力和游玩 183
人口的适当生命 184
保障流通安全 188
生命政治的伦理 196
bíos的技艺 203
自我和生命权力 213
bíos的实践 220
在此性的注意力 226
游玩的形而上学 231
审美、游玩、创造 237
造物、矛盾和德性 242
索引 249
提摩太·C.坎贝尔认为,要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就必须将生物权力的范畴拓展到纳粹集中营之外。他指出,现代政治通过具有侵入性的传播和消费技术来掌控生命,这些技术承诺让人免受死亡、残疾、无聊和孤独的困扰。坎贝尔将大众传媒和生物工程与全球小资产阶级的诞生联系起来,指出这一阶层的特点是令人恐惧的距离感的缺乏以及社区的不断瓦解。这本论证有力、引人入胜的著作,应当被所有对智能炸弹和云计算时代的集体生活的未来感兴趣的人阅读。
——朱莉娅·莱因哈德·卢普顿,《与莎士比亚一起思考:政治与生活随笔》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