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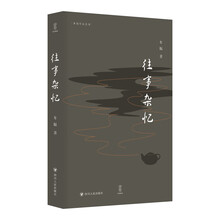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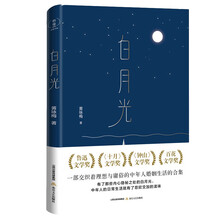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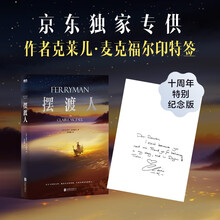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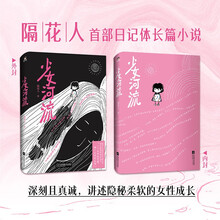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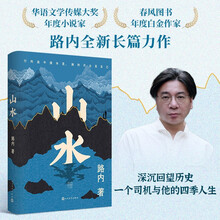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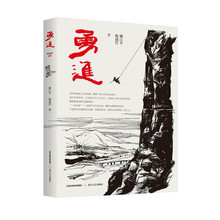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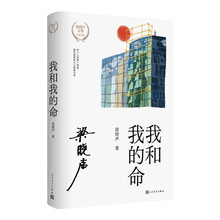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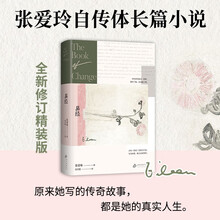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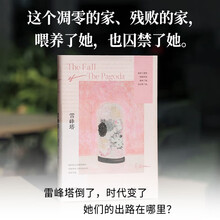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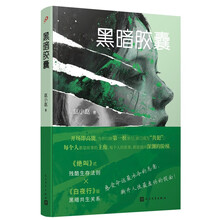
青年作家东来首部长篇小说
一首“小镇做题家”的悲歌,怎样的生活才值得一过?
l 教育是否是一场骗局?探讨“小镇做题家”的成长困境与出路。
“我没有原点可以回去,只能沿着道路向前。”
《凤凰籽》里,既有从小就按照精英教育培养的“天才少年”,也有渴望通过考试逃离,对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能做什么,一片混沌的“做题家”。从考试、大学专业选择再到就业,小说通过不同家庭背景的人的成长路径与人生选择,探讨“小镇做题家”该往何处去,反思了教育制度、阶级差异如何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路径的选择。
l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觉得留在小地方是输?
见识过城乡的参差,再也无法忍受匮乏生活的少年;因被指责“当代课老师没前途”,与家境优渥的好友决裂的“小镇做题家”;为了融入城市中产,改名换名的咖啡师……他们或时刻担心下坠,不能留在大城市生活,或巧言令色,如同《猫鼠游戏》中的模仿犯。主人公一面努力提升学历,改掉说话的口音,提升审美趣味,一面对城市生活怀有警惕之心,难以真正融入。当小镇的人带着家乡赋予的韧性和脆弱闯入都市,完成了前半程的“改命叙事”,如何在异地落地生根,如何在流徙中安顿自我,则是后半程更为复杂的命题。
l “做题家”的目标是成为中产吗?
“我”的养父母,杨爵和杜丽,一对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家中摆满书籍和世界各地淘来
的纪念品,在饭桌上讨论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却对眼前的苦难不置一词。他们曾是“我”艳羡的对象,为了成为这样的人,“我”改掉说话的口音,提高文学艺术品味,却始终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而相处越久,越能敏锐地捕捉到中产生活背后的脆弱、虚伪与不堪。从朝夕相处到冷淡疏离,“我”用肉身撕开他们的谎言,也迫使自己思考“何为良好的生活”。
l 贫穷和苦难是媒体赚取流量,愚弄观众的方式吗?
“我们生活在人和人无法互相看见的事实中。”
一个贫苦的少年带着带着逃离和改变命运的渴望,参与了一档综艺节目,与大城市生活优渥的少年互换了一个月的生活,在短时间体会到堪称惨烈的城乡对比后,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然而,节目播出后,他发现自己与家乡只是拿来展示城乡差距的猎奇对象,热点散去,再度无人关心。小说以戏剧化的结构探讨了地理与身份变迁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能否通过“真人秀”获得对社会的正确认知。
《凤凰籽》是青年作家东来的首部长篇小说。
一个乡村少年,带着逃离的渴望参加了一档“互换人生”的综艺,从此再也无法回到匮乏的生活。
只想赢,却不知自己能做什么的“小镇做题家”;在饭桌上高谈阔论,对眼前的苦难不置一词的大学教授;努力融入城市中产,改名换姓的咖啡师……主人公以肉身撕开人们的伪装,又将谎言视作抵抗偏见的武器。
从无知到略知,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我们注定要带着裂痕生活,正是这些裂痕,赋予我们生命的厚度。
“我没有原点可以回去,只能沿着道路向前。”
从腹地来的人——自序
动笔创作这部小说时,“小镇做题家”尚未成为公共语境中的热词。然而在长篇的写作过程中,这个词突然闯入视野,从最初个体自嘲的标签,逐渐演变为一代人的集体叙事。当编辑读完书稿问我“你写的是不是‘小镇做题家’”时,我哑然失笑——这看似偶然的耦合,实则是时代浪潮下无数人命运的共振。
我接受这一标签,却不愿将其等同于“失意者”。相反,在我看来,依靠“做题”走出小镇的人已然是命运的宠儿。只是人们惯于仰望高处,鲜少回看来路,便难以察觉自己的幸运,以及身后落下的更多同龄人。“做题家”们带着各自的小镇所赋予的韧性和脆弱闯入都市,完成了前半程的“改命叙事”;至于如何在异地落地生根,如何在流徙中安顿自我,则是后半程更为复杂的命题。
1990年,我出生在江西中部一个宗族村落。三千人的村庄同属一姓,人情与规则编织成密网,维系着费孝通笔下“乡土中国”的最后图景。江西是劳务输出大省,“打工”是日常生活出现最高频的词语,也是众多人赖以生存的手段,它深刻地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十岁以前,我目睹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迅速崩解;青壮年人逃离,老人和儿童留守,春节是村庄一年中唯一的沸腾时刻——候鸟般的打工者从各地归来,带回城市里的消息与钞票,也带回被小心折叠起的疲惫和不适应;旧的秩序、道德、生活方式摧枯拉朽,新的事物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建立和繁殖。财富重新分配,泡沫鼓胀又破裂,人群聚散离合,变化太快,有如劲风洪流,催逼着无数人向前,却不容人回顾。我的生命历程也紧紧贴合着经济起飞和城市化的浪潮,乘着风飘离故土,泊于上海。大城市的运转惯性容不得人停顿回眸,很快就能模糊掉人对时间的感知,二十年转瞬即逝,我在清晨醒来时常被某种失重感攫住——“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既割裂了血脉相连的乡土,又未真正融入齿轮链条中的都市,我不明白这种不安源于何处,止于何时。
不断地流徙,或许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处境。在上海,我结识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普通话和体面的谈吐让我们不分彼此,但各自迥异的成长经历和方言,又仿佛让我们置于平行时空。迁徙者的身份是一层透明隔膜,让我们既能窥见彼此的生活,又永远隔着一道无形的边界。我在同龄 人中体认到的这种割裂感,让我对奈保尔笔下的移民文学产生深切共鸣——《大河湾》我读过几遍,无论是跨越国境,还是跨出乡土,剥离故土的断裂、重塑身份的挣扎, 我与奈保尔笔下的人物本质上并无二致。我们都是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在陌生土壤里艰难抽芽,一路丢弃方言、生活习惯,甚至记忆,只为换取一张“现代都市人”的通行证。
写作长篇时,我常想起那些消失在分岔路口的同龄人,我和他们短暂交集,打过照面,曾是玩伴、亲友、同学。他们中有人考取大学,有人从商,更多人继承父母辈命运,继续栖身流水线,在外地艰难揾食;但我们早早彼此失落,成为无言的陌生人,互不相认。城市化,是一代人的城市化,也是每个人的城市化。连续性被粗暴地切断,踽踽独行的孤独难以克服。
能戴上“小镇做题家”光环的终究是少数,而更多人连成为叙事主角的资格都没有。在怀想中,我得以深感自己的幸运:作为女孩,江西女孩,竟能幸运地被家庭全力托举,沿着“读书—考学—去上海工作”的“正确路径”跌撞前行。这种幸运既让我愧疚,也让我警醒——当我们将人生简化为”逆袭”爽文时,是否正粗暴地抹杀那些未被看见的轨迹?
小说里的主人公从十二岁跋涉至三十岁,和我一样经历了乡土溃散、城乡碰撞、身份重构,但这并非我的自传。我采用了相当戏剧化的方式写作,一个贫苦少年被电视媒体粗暴地扔到大城市生活优渥的家庭,在短时间内感受到堪称惨烈的城乡对比,内心激荡变化,他的错愕和无措被媒体当成奇观展示,经历过城市的浮华洗礼,又被扔回山村老家,却再也无法逆来顺受。现下,一个人已经很少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这样极端的处境,更多的时候,面对的是外部世界变化导致的无法平息的内心激荡。这便是人生的基调了,经历过粗暴分裂的人更加懂得。
虚构是更自由的镜子,能映照出千万人的倒影。那些被遗弃的旧物、被淡忘的乡音、被时代碾过的微小个体,都在文字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写作如同考古,我不断从记忆废墟里打捞碎片:固守家园却被时代抛弃的男人、被撤销的乡村中学、对马桶的礼颂……这些细节或许微不足道,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站在三十五岁回望,我越发感受到潮流的蛮横之力。普通人如风中苇草,能做的唯有顺势俯仰。但写作让我获得回望的停顿,甚至反抗的尊严:当现实世界加速遗忘时,文字成了最后的保鲜剂。书中藏着我秘而不宣的幽暗——对逃离者的嫉妒、对留守者的愧疚、对都市精致主义的疏离,还有对故土既眷恋又渴望逃离的矛盾。完成书稿那日,我仿佛卸下背负多年的行囊。它是我蜕下的旧壳,是瓶中小人的重生仪式,更是对所有“迁徙一代”的告白:我们注定要带着裂痕生活,正是这些裂痕,赋予我们生命的厚度。
上 001
中 145
下 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