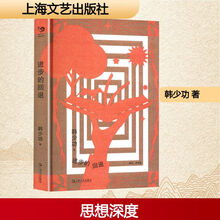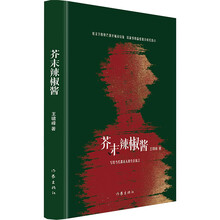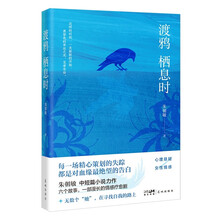《隐秘的河流》:
距离县城七十公里以外的铁城,洮河水将它条状的地形一分为二。每逢初三和初八是铁城最热闹的集市。如果在夏天,河对面村寨里的人会扯着一艘笨重的木船抵达铁城赶集市。冬天的时候更方便,当洮河封冻了的时候,河对岸的人会背着柳条编织的背篓,赶着驴车,拉着骡子,马背上搭着褡裢,老老少少,热热闹闹,来对岸采购。
嘈杂的人群里,一方小小的桌子,顺桌子的桌角边放着一台破旧的录音机、黑白彩色电视机、矮小的冰箱。桌子上凌乱地摆满着元器件。桌前立着一个褐色的硬纸板,上面用黑粗的毛笔醒目地写着“修家电”几个大字。这是庆云叔叔支在我们家大门口的摊位。
人群中的庆云叔叔穿咖色的帆布夹克,青色的裤子。他埋头拆卸着一台18英寸的电视机,电视机凸出的后盖被打开,那些五颜六色的电线像大脑里的血管一样错综复杂。他低着头认真梳理着那些在我看来永远也没有章法的电线,浓密的头发直直地垂在额前,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折射出栗色的光泽,而光的阴影正好打在他英挺的鼻梁上。
他见我顶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从大门出来,便停下手中的活,从旁边的包子店里买给我两个羊肉包子。我哈着气站在他的摊位前,边吃包子边看着他从包里拿出那些长短不一的改锥,然后再将一些大小不一的螺丝钉倒在方形的铁皮盒里,继而又开始认真地捣鼓桌面上那些凌乱的电线。
庆云叔叔是父亲远房的一个表亲,他家住在村子的东头。风吹过峡谷的时候,他家大门顶白色的玛尼旗被大风吹得哗啦啦直响。他们家是一进三院的模式,刚进去是一顺溜的草屋和庆雨叔叔用来码放洮砚石原料和制作洮砚的敞篷。第二道门进去是紧凑的一嵌套土坯木梁的房屋,院子里干净整洁地铺着洮河边捡来的鹅卵石。他的父亲将那些石头按颜色排出菊花样的图案,廊下的台阶也用那些鹅卵石精心垒砌起来。
我的表姑奶奶是个皮肤白净的微胖妇人,虽然年事已高,但她一头乌黑的发在灰色的头巾下还是那样顺滑。表姑奶奶的干净整洁是出了名的,用奶奶的话说,她家的地面能照出人影来。
庆云叔叔还有个哥哥叫庆雨。他在闲暇的时候用洮砚石废料给我雕刻过一只精瘦的石猴。他的妻子是个爱笑的小眼睛的女人,眉宇间稍稍带有一点媚气。在风中,她总喜欢坐在院子的廊檐下织一件酒红的毛衣。我一直见她织,可总觉得没有织完的时候。
“哎呀,丫丫来看你姑阿婆了。”我进去的时候她的手里不停地织着那件酒红色的毛衣。她愉悦地笑着,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细细的褶皱。她的眼睛远远地向我瞟过来,用余光顺带仔仔细细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遍。我最不喜这样被人莫名其妙地打量上一番,我最怕那样随意又刻意的眼光,仿佛永远藏着天大的预谋。
我快速地从上屋最左侧的小门穿过。穿过一道黑色的狭窄的夹道就来到了一座占地两亩左右的大果园,果园里错落有序地种着梨树、杏树、苹果树,还有零星的几棵桑葚树,那些树的枝丫在风中不停地摆动着,发出“吱吱”的声响。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一直通向靠山脚的五间土木屋。还没进门就闻见一股淡淡的柏木香,这味道会让我想到河对岸原始森林里特有的清香,也会想到正月十五在山顶拜祭山神时煨起的桑烟,风一吹,那些柏木燃烧后的味道飘得满谷满洼都是,那种味道闻起来古老中略带一丝隐秘。
整个村寨,表姑奶奶的发糕蒸得最好。我进去的时候她正从蒸笼里将白净的发糕搬放在桦木的案板上,然后在切得方正的发糕上淋上调制好的蜂蜜。她见到我总是露出比发糕还甜的笑容。表姑爷坐在用山羊毛擀成的黑色毛毡上,在擦得锃亮的火盆沿上悠闲地喝着罐罐茶。他喝茶的时候总是将屋子里的花窗支起来。风一吹,那些茶香都被带上了天空。表姑爷喜欢用他粗糙的手指捏我冰凉的鼻子。“丫丫是个好姑娘,就是总也不爱说话,也难怪你总喜欢来找你庆云叔叔。”表姑爷说完,抽上一口羊骨做的旱烟,仰起头望着头顶熏得微黑的木梁。
“不要拿丫丫和庆云比,丫丫不是哑巴。”表姑奶奶显得很生气。
“哑巴也有哑巴的好,至少不会祸从口出。说得少就想得多,你看我家庆云,除了不会说话,那脑瓜子、那长相不比村里其他孩子差。”坐在炕沿边的表姑爷说完这句话,好像找到了些许的宽慰,使劲抿了一口罐罐茶。
走进庆云叔叔的房间,他正埋头认真地维修着上个集市上的一个破录音机。他修好后,将手掌轻轻挨在喇叭上感受它的震动。
阳光很好,庆云叔叔也支起了花窗,吹过峡谷的风裹挟着洮河水的湿气涌进了窗户。他打开抽屉,从里面给我找出打磨光滑的石子。我开心地接过那些礼物,对着他张着嘴做出谢谢的嘴型,他微笑着摸摸我的头。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眸中涌动的纯真和热情,让我觉得如果真有上辈子,我想我或许也是一个哑巴,要不就是大河边上的一棵树,孤独安静地存活在世上。在风里,在寂静的岁月里,我看到河对岸另一棵树静静地伫立在艳蓝的天空下,在风中我们隔岸致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