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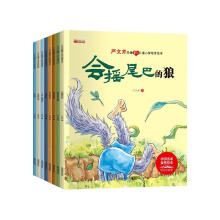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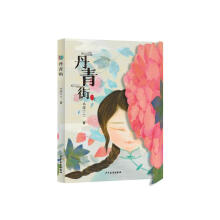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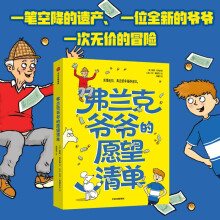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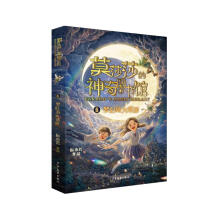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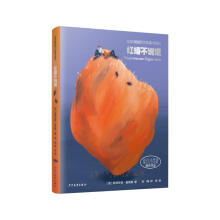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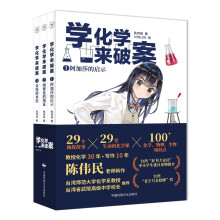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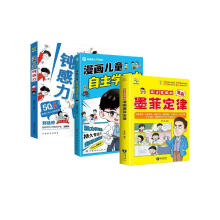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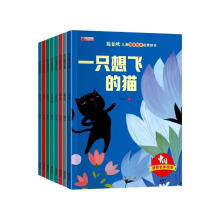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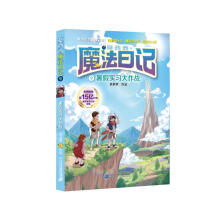
本书主人公尼茨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同学米沙是他眼中最棒的朋友。米沙对动物有着超于常人的了解,据他所说,他妈妈是一位常年在雨林做研究的生物学家,经常会写信回来告诉他动物的知识。而他的爸爸总打扮得超酷,还会讲故事,这让米沙受到了班里其他同学的羡慕。故事始于尼茨一个怪异的发现:米沙为了逃避游泳课,竟谎称自己对氯气过敏,还伪造了一份医生证明。为了揭开米沙说谎的真相,好奇的尼茨展开跟踪¨¨¨两个好朋友之间的友情发生了危机,米沙的谎言败露,无法面对昔日的好哥们,而尼茨在短暂的迷茫之后,制定了一个帮助米沙的计划,经过众人相助,米沙的生活终于重现阳光。
以前,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米沙总会吓唬鸭子玩儿。每当冬去春来,冰雪消融,我们就会捡拾堆在路边的碎石子,待两手抓满石子,我们就悄没声儿地靠上去,直到距离鸭子只有十步之遥的时候,猛然大喊一声“呜啊”,同时奋力将手中的“炮弹”扔向池塘,顿时湖面上噼啪作响,就像下雹子一般。
受到惊吓的鸭子们拼命拍打着翅膀,嘴里“嘎——嘎——”地叫着,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远远望去,它们就好像在水面上奔跑。在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当你不再相信这群鸭子能成功逃脱的时候,它们居然飞离水面,腾空而起。我和米沙就在后面看着鸭群拍打着翅膀,离开水面,四散飞走。
这成了我们每天放学回家路上必定要玩的游戏。记得有一次我们听到牧师讲耶稣履海的故事时,米沙小声地对我说: “这算什么能耐?连鸭子都能在水上跑呢!”说完这句话,米沙的表情没有半点变化,一如往的平静和严肃,而我忍不住扑哧笑了,因为我的脑海中立马闪现出耶稣在水面上奔跑的场景:撅着屁股,挥舞着双臂,嘴里叽里呱啦,活像只鸭子——这幅画面实在太搞笑了!
那时,我的想象力就已经很丰富了:每当我在脑中想象某个事物时,它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栩栩如生,比如像鸭子一样在水面上奔跑的耶稣。一想到这儿我就忍不住要笑,而牧师只能一脸怒气地瞪着我。当然了,他的怒气只针对我,并不针对米沙。在他眼中,米沙是一个上课认真听讲的模范生。牧师绝对不会相信米沙会和周围的同学交头接耳,说些污言秽语。米沙对任何问题都回答得恰如其分,而我那时就已经患上了多动症,没事儿总挨批。
那会儿,我还没开始写打油诗,也没有开始用押韵的语句来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直到过了段时间我才发觉,原来自己的脑子能够调动词汇,将它们谱成韵文。
在我看来,韵文是口述音乐,是通过带有节奏和韵律的文字展现的音乐。当你试着押韵时,你的大脑会进入一种疯狂的节奏,仿佛你在和你的大脑共舞。一个屁股扭来扭去的人会有一个跳舞的大脑是不是不符合逻辑?
自从我发现这种文字音乐的表现形式后,许多押韵的词句真的会不知不觉地钻入我的脑海,不仅有单音节押韵,还有复杂的多音节押韵。
以前,大家都觉得我只不过是个爱吹嘘的人,但自从我开始说韵文,他们对我要说的话总是充满期待。如果你一直在那里喋喋不休,那么来一段诗文听起来显然要比说话不押韵好得多。
有人说我在朗诵诗歌,还有些人管我的韵文叫说唱。米沙称其为打油诗,尼茨式打油诗(尼茨就是我)。如果让我现在开始讲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那我就得补充一点,接下来这个故事所涉及的许多打油诗都是我和米沙一起创作的,所以,实际上这些韵文应该是尼茨 — 米沙式打油诗。它们是让我写下这个疯狂故事的原因,与其说是我的故事,不如说是米沙的故事。在米沙看来,如果一个人要公开自家的一些令人讨厌的尴尬事的话,不如用一种有声有色的方式来向别人讲述。“讲讲这个故事吧,”米沙对我说,“我没意见,你讲吧。但尼茨,你要让这个故事听上去有声有色!”
米沙一直叫我尼茨,其他人也跟着他这么叫。当然,我喜欢别人这么称呼我,因为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