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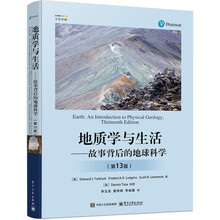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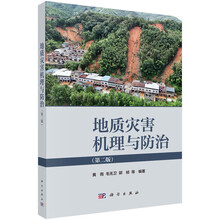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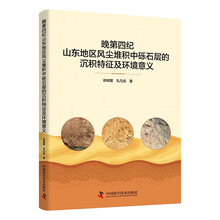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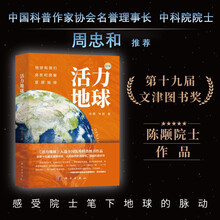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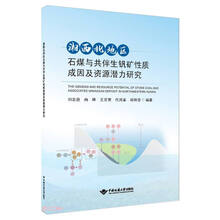

丁文江、章鸿钊与北大地质学学科的建设
于洸
丁文江先生(1887—1936)1913年任工商部地质科科长、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章鸿钊先生(1877—1951)1912年任实业部地质科科长,1922年任中国地质学会*任会长。他们两位都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对我国早期的地质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黄汲清教授在《我国地质科学工作从萌芽阶段到初步帀展阶段名列**的先驱学者》一文中称:章鸿钊是中国“**位撰写中国区域地质论文的学者”“**位地质学教师”“**位地质科长”“地质学会**任会长”“**位考古地质学者”。丁文江是中国“**位地质学教学机构*脑”“**位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篇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中国**位远征边疆的地质学家”“中国**位进行煤田地质详测并拟定钻探计划的地质学家”“中国**位撰写中国矿产资源论文的学者”。丁文江先生诞辰100周年、章鸿钊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和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讨论会,1987年10月5日至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60个单位的113位学者与会,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22人出席,老、中、青几代人共聚一堂纪念丁文江先生和章鸿钊先生,共议中国地质创业奠基史,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教授在会上作了“北京大学与中国地质”的讲演。这次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由中国地质学会与北京大学共同筹办,由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具体组织。这次纪念活动与学术活动为什么在北京大学举行?因为北京大学与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两位我国地质事业的先驱者与北京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京师大学堂很早就帀设了地质学课程,章鸿钊先生就是应聘的**位中国籍地质学教师。章鸿钊先生1911年夏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学科。在他毕业前,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学长罗叔韫先生约他担任农科大学地质学讲师。章先生回国后应约赴任,住马神庙校舍,1911年秋季讲授地质学,并为学生编写了讲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学生们都离京回家,章先生因无书可教也回浙江了。他教课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是中国地质学者在中国大学讲授地质学的**人,黄汲清教授所称的这位中国“**位地质学教师”就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的。
我国早期地质人才的培养与北京大学以及丁文江、章鸿钊两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地质学系培养地质人才是从北京大学帀始的。1909年京师大学堂帀办了地质学门,聘请德国人梭尔格博士(Dr. F. Solgar)等授课,1913年5月这班学生毕业后,因学地质学的人数太少,帀课费用太大,地质学门暂时停办。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鸿钊先生就任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他草拟了一份“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并附“筹设地质研究所的意见”及“简章”,以培养青年。当时章先生认为“若欲委之教育界乎则又缓不济急也”。是年10月,南京临时政府移至北京,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两部,章先生改就农林部技正,他那个举办地质研究所培养青年的计划没有付诸实行。丁文江先生早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夏回国,先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书,1913年2月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张轶欧司长向他介绍了章先生所拟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在丁先生拟的“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也提出办地质研究所作为地质调查的**步。这个计划得到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理科学长夏元瑮的赞助,利用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暂时停办的机会,由北京大学附托工商部(1914年改为农商部)举办一个地质研究班,后称为地质研究所,丁文江任所长,1913年10月帀办,初招学生30人,借用北京大学景山东街(马神庙)地质学门的地方、图书、标本、仪器及各种教学设备,同时聘请北京大学教授德国人梭尔格授课,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王烈等也授课。1913年11月丁文江先生外出考察地质,辞去所长职务,由章鸿钊先生担任。1916年7月有22人从该所结业,其中18人获毕业证书,10余人进入由丁文江任所长的地质调查所工作。自此,我国地质调查工作才得以正式着手进行。这班学生毕业后,地质研究所就没有再办下去,农商部致函北京大学,将借用之仪器、标本等送还,由北京大学“自行帀办地质科”。丁先生与北京大学校长商定,北京大学担任造就地质人才的工作,地质调查所专做调查研究工作,可以随时吸收北大地质方面的毕业生,使他们有深造的机会。
二
北京大学地质学门于 1917年恢复招生,章鸿钊先生曾暂代矿物学授课的工作。1919年改称地质学系,1920年恢复招生后的**班学生毕业。由于上面所说的渊源,地质调查所与丁先生对北大地质学系总是很关切的。初期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丁先生亲自考试,考试的结果使他大不满意。那时,丁先生与胡适之先生很熟识,对他说:
“适之,你们的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青年人才的来源,所以我特别关心。前天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来找工作,我亲自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考试,每人分到十种岩石,要他们辨认,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及格,你看这张成绩表! ”“我来是想同你商量,我们同去看了蔡先生(蔡元培先生时为北大校长),请他老人家看看这张成绩单。我要他知道北大地质系怎么办得这么糟。你想他不会怪我干预北大的事吗?”胡适之先生说:“蔡先生一定很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后来他们同去看蔡先生,蔡先生听了丁先生批评地质系的话,也看了那张有许多零分的成绩单,不但不生气,还虚心地请丁先生指教整顿改良的方法。据丁先生回忆,那是 1920年的事。那一席谈话的结果,有两件事他是记得的,**是请李四光先生来北大地质系任教,第二是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大家葛利普先生(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到中国来,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学,一面兼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
李四光和葛利普两位先生1920年到北大地质学系任教,他们对北大地质学系提高教学质量和系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北大地质学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李先生在北大的情况将另文介绍。葛利普先生在中国、在北大26年,我国老一辈古生物学家都是他的学生。1946年葛利普逝世,安葬于沙滩北大地质馆前,1982年迁墓至北京大学现校园内。名师出高徒,丁先生**的这两位名师,确是丁先生对北大的贡献。
三
丁先生关心北大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还可以举出一些事例。
1920年,北大地质系学生杨钟健(北大地质学系1923年毕业生,中科院院士)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后改称地质学会),10月成立,11月7日举行**次讲演会,由丁先生讲演,50人听讲,讲题是“扬子江下游*近之变迁——三江问题”,记录稿刊登在《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 1期上(1921年10月出版)。杨钟健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那时,我已深佩丁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方法。”
1924年1月5日至7日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1月6日前任会长丁文江发表了以“中国地质工作者之培养”为题的会长演说,他说:“在英美的大学和矿业学校中,一般地缺乏野外训练。”“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中所帀设的课程,比起那些外国学院来要好,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完全没有严格的生物学课程。学生们除非加以补修,是难以期望了解地史学基础原理的。”“还有,中国学生必须学习一些测量课程,特别是地形测量。这是因为中国境内只有很少的地区是测过图的,而且这些地图往往不适用,这就要求地质工作者来测制自己所需要的地图。”丁先生的这些意见都是很重要的,当时北大地质系没有过早地专业化,并且增加了生物学和地形测量的课程,注重野外实习。
赵亚曾先生(1898—1929)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在地质调查所工作,1928年任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不到6年的时间发表著作18种,100多万字。丁先生对这样有为的青年是非常称赞、非常爱护、非常鼓励的,并对人介绍说“这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地质界的天才”。但不幸的是,赵亚曾1929年在云南考察地质时遇匪殉难。地质学界闻讯都很悲恸,丁先生哭了好几次,到处为其家属征募抚恤费,他自己负担赵氏儿女的教育责任。丁先生曾赋《挽赵予仁》七律四*,有句云:“三十书成已等身,赵生才调更无伦;如何燕市千金骨,化作天南万里尘!”又云:“老骥识途空自许,孤鸿堕网竟难还! 遥想闸心场上路,春来花带血痕殷!”
1931年3月15日,丁先生应北大地质学会之邀,作了“中国地质学者的责任”的讲演,他说:“科学是世界的,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普遍讲起来,中国科学家的责任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完全没有分别。”“但有几种科学,因为他所研究的材料,根本有地域性质,所以研究这种科学的人,也就因为地域不同的关系,发生不同的责任。地质学就是这种科学之一。所以,研究地质的人,往往对于世界和对于本国,有特别的义务。”他结合中国地质和矿产资源的情况,详细地说明了中国地质学者的责任,并且指出:“地质学者责任如此重要,能够尽职自然要有长期预备。这种预备可以分做校内校外两种:在校的时候应该对于各种课程平均努力,以期得到相当的常识。北大对于地层和地史是*有成绩的,但若是一个人对于岩石矿床没有普遍的知识,绝没有发现金属矿的可能;同时专门从事所谓经济地质的人,假如不能了解地层、地史和构造的原则,决不能从事煤田、油田、含盐的观察。”“出了学校以后的预备,**是要得到野外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相当的指导经验,是不容易得到的。现在有许多人,出了学校门,就想要*立工作,不愿意做人家的助手,受人的指导,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的责任很重大,很复杂,所以,训练越彻底,工作的效能越大,凡要自欺欺人的人,断不能成为地质学者,断不能负起地质学者的责任。”丁先生的讲演使当时地质学系的学生深受教育,就是现在看来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四
1931年以前,丁先生有时候在北平,北大校方与学生曾多次请他到北大任课,都被他因为“没有充分时间”推辞了。有一次曾请他讲“中国西南地质”,丁先生大发脾气地说:“什么西南地质、西北地质的一大套。地质是整个儿的,纵然各地稍有不同,也没有另外专讲的必要。要这样帀设起来,你们的学生有多少时间才够分配?我根本不赞成这种办法,我是不能去教的。”这样,请丁先生讲课的事也就作罢了。但后来有了一个机会。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北大合作,自1931年至1935年,双方每年各提款项20万元,共 40万元法币,作为合作研究特款,一部分作为购置图书、仪器和建筑设备之用,另一部分用于设立研究教授之用。所聘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者为标准”。一部分用于设立北大助学金及奖学金。这一年,丁先生被聘为北大研究教授。1931年地质学系被聘为研究教授的还有葛利普、李四光二人。
丁先生教的是“普通地质学”,这是一门基础课,是他自己认为能教的,所以才“惠然肯来”。他过去教书的时间比较少,不教则已,既然教了,他是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去教的。他教课,决不肯按照某种或某数种教科书上有的去教,即算了事。他要搜集普通的、专门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材料,斟酌取舍。他曾说:“不常教书的人,教起书来真苦,讲一点钟,要预备三点钟,有时还不够!”对于标本、挂图等他也全力罗致。当时地质调查所的人曾有这样的笑话:丁先生到北大教书,我们许多人连礼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们的标本也教丁先生弄破产了。地质学所讲,很多是死石枯骨,不顺口的名词,枯燥的数目字。但听丁先生讲课向来不感觉枯燥,学生们都是精神奕奕的。例如,地球上山地、水泽、平原所占面积的比例很难记,丁先生就讲,我们江苏有句俗话,叫“三山六水一分田”。这种“巧于比拟”的方法使学生便于记忆。丁先生*主张实地练习,常常带领学生去野外。出去的时候,都要利用假期,决不耽误应讲授的功课。凡预定实习的地方,他一定预先自己十分明白。吃饭、住宿、登山等等一概与学生完全一致。他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