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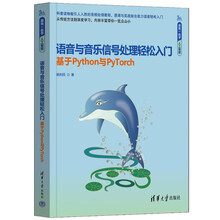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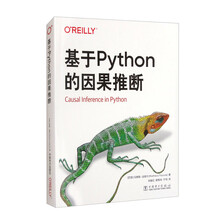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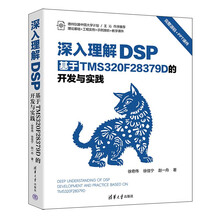
本书记录了60多种行将成为历史的老手艺、老行当,用简朴的语言描写了曾经游走在乡土中国大地上的老手艺老行当人的酸甜苦辣、生老病死,将正在渐渐消逝的传统生活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全书从个人记忆切入,通过大量、扎实的实地访谈、田野调查,重现老手艺的彼时彼景。知名漫画家邓辉华为本书绘制的漫画插图,寥寥数笔,生动传神。此外,修订版在初版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饰润色,每种行当都补充了民谣、民谚等传统文化的内容,并增加了凝练手艺精髓或点破行当辛酸的竹枝词。
弹 匠
人道厅堂陪少娘,不经风雪不经霜。
炎炎夏日汗如雨,飞絮飘飘总闭窗。
小时候,小孩子最喜欢看师傅弹棉絮,当作好玩的游戏。雪白的棉絮,像一层厚厚的积雪;光滑的弹槌,像一颗手榴弹;圆圆的磨盘,像一个锅盖;弯弯的木弓,弹起来像一曲叮叮咚咚的民乐。
“千匠万匠,要学弹匠,住格大厅堂,陪格大少娘(姑娘)”,这句俗谚说弹匠长年在厅堂里弹棉絮,不用风吹雨淋日头晒,还有姑娘帮着拉纱线,令人艳羡。不过,弹匠也有自己的苦恼。棉絮轻飘,遇风飞扬,夏天也不能开窗,又闷又热,大汗淋漓,只能用手掌捋一捋、甩一甩,或用毛巾擦一擦。一天棉絮弹下来,眉毛胡子一片白,直到收工才能洗澡。即使戴口罩,也难免吸入棉絮,天长日久,易得硅肺。与漆匠一样,弹匠每天晚上收工后,都吃猪血,以便清肺。
与普通手艺人比,弹匠的工具很特别:一把木制的弓,四五尺长,两头装弦处向前微翘,耐磨的牛筋做弦,有纳鞋底的苎麻线一般粗;一只木制的弹槌,尺把长,用来弹弓上的弦;一个圆木磨盘,五六寸厚,多用硬木做成,用来压实蓬松的棉絮;一个顶端带有叉线凹槽的竹竿,用来给棉絮拉线。
弹匠把皮棉堆在木板上,把一根富有弹性的竹竿绑在身上,再用绳子把竹竿和弓背连在一起,这样,弹弓就悬在皮棉的上方。弹棉花的时候,弹匠左手握木弓,轻轻下压,右手执弹槌,敲击弓弦,发出“嘭嘭啪啪”的声音。那根颤动的弓弦,像着了魔似的,一粘皮棉,就弹成絮状。家乡有个谜语“驼背佬,钓田鸡,花花姑娘满天飞”,谜底就是弹棉絮。
弹好棉絮,拉上四层网线,横一层、竖一层、斜两层,纵横交错,成“米”字形。由姑娘帮助拉线,她们眼睛明亮,手指光滑,动作灵活,得心应手。如果换作老大娘,老眼昏花,皮肤皲裂,去拉那根又细又轻的纱线,碍手碍脚。这是“陪格大少娘”的原因所在。郑宅公社东明村的铁匠柳锡友年轻时曾到绍兴诸暨弹棉絮。当时,有位姑娘帮他拉纱线,一来二往,暗生情愫。后来,姑娘跟锡友师到浦江一看,家里只有一间矮房,一贫如洗,就知难而退了。
农家喜欢图吉利,讨口彩。作为嫁妆的棉絮,配以红绿两色纱线,还要装饰“囍”“花好月圆”“百年好合”之类吉祥文字,配上“双钱”、中国结等吉利图案。
前吴公社罗源村的弹匠于崇斌生于一九四九年,个子虽小,但手脚麻利,人称常山赵子龙。他别出心裁,在棉絮上面装饰鸳鸯戏水(寓意夫妻恩爱)、并蒂莲子(寓意夫妻和睦)、石榴(寓意多子多孙)、松鹤(寓意健康长寿)等图案。还要在棉絮里扔几粒棉籽,寓意多子多福,大吉大利。有时,两个弹匠在同一个厅堂弹棉絮,两户人家的女儿东看看,西瞧瞧,看到崇斌师弹的棉絮图案丰富、寓意吉祥,主动要求他来弹自己的棉絮。
嫁女儿的人家爱体面,讲利市,招待弹匠有酒有肉,还要泡糖茶,烧荷包蛋,付了工钱,还送红包,少则两角,多则五角。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行情。
弹棉絮虽说靠技术吃饭,也要懂一点生意经。有一年,崇斌师到人生地不熟的建德下梓洲村弹棉絮。一天晚上,大队支书出门开会,女儿参加俱乐部活动,家里只留老婆一人切花草(即红花草,紫云英)。他主动上前搭讪,帮她磨菜刀,切花草,忙到深夜十二点。无事不登三宝殿,支书老婆看透他的心思,就问:“客人,你帮我磨菜刀、切花草,有什么要帮忙的吗?”他答得不卑不亢:“我在你们村里弹棉絮,欢迎你有空来看看。”支书老婆说:“不用看了,你菜刀磨得好,花草切得快,弹棉絮的手艺肯定好。”恰逢支书女儿即将出嫁,正要请人弹四床棉絮,这桩生意由崇斌师承揽了。从此,他在下梓洲村打开市面,生意越来越好,一个人忙不过来,最多的时候带了六个徒弟。
崇斌师学弹棉絮时,师傅已经七十三岁,规矩严,脾气大。在东家吃饭,要徒弟左手拿碗,右手持筷,腋下夹紧,不能大模大样,碰到身边的人,也不能发出一点声响。有一次,一个徒弟吃面时发出声响,师傅破口大骂:“君子吃面牙咬断,没声响。”师傅一辈子带过十四五个徒弟,大多忍受不了他的臭脾气,半途而废。本来要学三个月,崇斌师学了两个半月,技术到手,就逃回家了。
郑宅公社丰产村的郑寿廷生于一九四二年,一辈子弹了四十五年的棉絮。第一年,他给师傅白做做;第二年,师傅每天给他开五角工钱。当时,弹一床新棉絮的工钱是一元五角,师徒俩一天弹两床新棉絮,工钱三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弹一床新棉絮是一工,弹一床旧棉絮也是一工,多加五角工钱。
弹棉絮是半年忙、半年闲的行业,生活集中在下半年棉花采摘后。生产队里同意寿廷师出门弹棉絮,上缴三十元钱,换取自由身,不计工分。
按行规,弹匠半夜三更就要起床,连夜赶路,到东家门前等天亮。有时候,人在前面走,仿佛有人在脚后跟撒泥沙,回头瞧瞧,不见踪影,疑神疑鬼。有一次,寿廷师在绍兴诸暨干活,纱线用完了,吃好晚饭,翻山越岭,走了三十里山路,连夜赶回家里,叫老婆纺好纱线,第二天再赶回去,到东家时天都快亮了。
后来,看到电影《鬼子来了》里有一段很逗人的情节:小学音乐教师出身的日本少佐,把弹棉絮的弹弓误识为乐器,让弹棉郎演奏。弹棉郎唱了一曲弹棉絮的歌:“弹棉花啊弹棉花,半斤棉弹成八两八哟。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哟,弹好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看着这熟悉的场景,听着这熟悉的声音,我差点笑断肚肠筋。
如今,商场里卖多孔被、羽绒被、丝绵被,品种繁多,蓬松柔软,轻便舒适,保暖性好,传统的棉被越来越少,弹匠快要绝迹了。
——选自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修订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
在我还小的时候,那些真正的劳动者——他们是走村串户的货郎,炸爆米花的外省男人,弹棉花的驼背,以及做衣服的,收长头发的,阉猪的——过着动荡或半动荡的生活,在大地上奔走,以不同的方式养活自己及家人,艰辛却充满尊严。
——草白
王向阳对故土的深情,对文化的打捞,不是怀旧,而是传承;不为过去,而是为未来。
——周华诚
手艺一道,蕴涵着文明的累积和嬗递,它们在物品上所留下的痕迹,反过来又为手艺塑造了不灭的形象。因此,手艺背后,虽然隐藏着苦楚、规矩和窘迫,但真正值得称道的,还是王向阳心中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潘江涛
岁岁年年,手艺人游走于乡村,像火把一样,温暖并照亮着一个又一个村庄。他们是村庄流动的血脉,打造着乡村的卑微与神圣,粗陋和质朴。
——陈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