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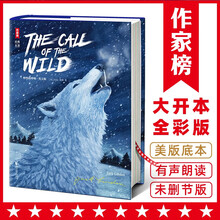
☆马丁·艾米斯是英国当代文坛的代表作家,与麦克尤恩和朱利·巴恩斯齐名。译文社将出版13本马丁·艾米斯作品,这是第二本。
☆文坛顽童、风格巨匠马丁•艾米斯以侦探小说为外壳,探讨了“死亡”议题
我是一名警察。这么说感觉好像要做什么特别的声明,或暗含某种不寻常的意义,但它只是我们习惯的说法而已。在我们这行,我们不会用“我是男警”或“我是女警”或“我是警官”这样的说法,我们只会说“我是警察”。我是一名警察。我是警察,而我的姓名是迈克·胡里罕,职位是警探。此外,我还是一个女人。
现在我要讲的,是我所遇过的最糟的一件案子。“最糟”这两字,在我看来,当你身为警察之后,就变成一种颇有弹性的概念。你难以固定“最糟”两字的定义,它的疆界每天都在不断往外扩展。“最糟?”我们会这么说,“根本没有‘最糟’这种东西。”不过,对迈克·胡里罕警探来说,这件案子就是最糟的一桩。
刑事侦查局位于市中心,这里有三千位同仁,分成许多部门、科室、小组和分队。这些单位的名称可说变化多端:组织犯罪、重大犯罪、人身伤害、性侵害、窃车、票据欺诈、特别调查、资产没收、情报、缉毒、绑架、闯空门、抢劫……以及谋杀。这里只有一扇扇上面标有“罪”的玻璃门,却没有一扇标有“孽”的玻璃门。犯罪的市民是攻击的一方,而捉贼的我们则是防卫的一方,这就是一般人的看法。
关于我个人生活的“十张牌”西方流行以塔罗牌占卜,作为反映个人过去生活及预示未来的工具。作者说的“十张牌”可能是指塔罗牌的十字占卜法,每张牌都含有重要的讯息。
是这样的:十八岁那年我进入皮特·布朗大学攻读刑事司法硕士,但我真正的志愿是第一线的工作。我按捺不住,便去参加州警考试、边境巡警考试,甚至参加监狱管理员的测试。我全都考上了。我还参加警察特考,结果也一样通过。所以我离开皮特·布朗,进入警察学校就读。
刚开始我在南区担任巡警,成为四十四街治安维护部门的一员,我们徒步或驾警车巡逻。后来我到“老人抢劫案组”待了五年,其间我积极办案,主动出击伪装诱捕,这让我得以晋升为便衣警察。之后,我又通过测试,佩上盾形警徽调至市中心。目前我在“资产没收组”服务,不过在这之前我在凶案组待了八年。我办过不少命案,我曾经是个专办命案的警察。
用几句话来形容我的外貌吧。我的体型遗传自我的母亲,她可以说走在她那个时代的前端,形象看起来颇似今日言必及政治的女性主义者。我妈几乎可以在那种以核战过后为背景的公路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出现一种以汽车和公路为典型叙事元素的电影,其主人公的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展开往往和公路息息相关。
中,扮演穷凶极恶的恶汉角色了。我还遗传了她的声音,而且经过三十年的尼古丁熏陶后,这声音低沉的程度更加严重。我的相貌遗传自我的父亲,这张脸很乡土,平淡无奇,一点也不城市化,不过我的头发倒是金黄色的。我在这座城市的“月亮公园区”出生,在这座城市长大,但后来遭逢变故。十岁那年我便由州政府接手抚养,迄今我仍不知我父母人在何方。我身高一百七十七公分,体重八十一公斤。
有人说最刺激的部门就是缉毒组(脏钱也最多),而公认最有乐趣的部门则是绑架案组(如果美国的谋杀案多半是黑人对黑人的话,那么绑架案则多半是帮派对帮派)。性侵组有它的支持者,扫黄组也有其信徒,而情报组正如其名(情报无远弗届,揪出匿影藏形的坏人),不过,所有人都默认凶案组是老大。凶案组才是真正的主角。
在这座规模属于第二级、因那座日本人出资兴建的巴别塔、港口码头、大学、最具有前瞻性的公司(计算机软件、航天科技、生化制药)、高失业率以及灾难性的纳税市民搬迁而小有名气的美国城市作者虽自创地名街名,刻意模糊作为场景的城市,但由这段叙述可推测极有可能为美国西岸大城西雅图。
,一个凶案组的警察每年可能要侦办十几件凶杀案件。有时你是这件案子的主要调查员,有时你则担任副手。我承办过的凶杀案件至少上百,破案率则刚好高于平均值。我能鉴识刑案现场,而且不止一次被称为“优秀审讯员”。我的文书工作做得棒极了,当我从南区调到刑事侦查局时,每个人都以为我写的报告只有区级程度,但其实我老早就具有市级的水平了。不过我还是精益求精,追求百分之百的完善。有次我完成一件非常、非常令人满意的工作,针对发生在七十三街的一起棘手命案,根据两名同为目击者和嫌疑犯的口供,整理出两份针锋相对的笔录。“比起你们这些人给我看的东西,”亨里克·奥弗玛斯警司拿着我的报告,在所有组员面前说,“这才是他妈的雄辩,这是他妈的西塞罗全名为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雄辩家。
对罗伯斯比尔全名为马克西米连·佛朗索瓦·马里·伊西多·德·罗伯斯比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是雅各宾派的实际首脑及独裁者。
。”我竭尽所能,务求完美。在我的警察生涯中,我大概处理过上千件不明原因的死亡案件,而其中大部分被证明为自杀、意外事故或疏于照料致死。因此我几乎什么场面都见识过了:跳楼的、分尸的、掩埋的、沉在水中的、浑身是血的、浮在水面的、举枪自尽的、爆炸致死的。我见过年仅一岁被棍棒殴死的尸体;也见过九十岁还被轮奸杀害的老年妇女的尸体;我还见过陈尸甚久,只能靠秤蛆虫重量以推测死亡时间的尸体。然而,在我所见过的这些尸体中,没有一具像珍妮弗·罗克韦尔的尸体那样,让我刻骨铭心,难以释怀。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即将开展的故事的一部分。我认为有必要事先交代一下我个人的历史背景。
到今天——四月二日——我认为这件案子已经“解决”——它结束了,完成了,被放下了。但是,这件案子的解答却引出更复杂的问题。我已经把一个打得很死的结,松成一堆乱七八糟的线头。今天傍晚我将和保利见面,到时我会问他两个问题,而他会给我两个答案,然后一切就算了结了。这件案子是最糟糕的一件。我纳闷:只有我这么认为吗?但我知道我是对的。事情正是如此,千真万确,没有半点虚假。保利是这个州的“切割手”,我们是这么称呼他的。他为州政府做切割,他解剖切开人们的身体,然后告诉你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我得先说声对不起,为我所使用的不当言语、不健康的讽刺和我的顽固而道歉。所有警察都是种族主义者,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纽约警察恨波多黎各人,迈阿密警察恨古巴人,休斯敦警察恨墨西哥人,圣地亚哥警察恨印第安人,波特兰警察恨爱斯基摩人。在我们这里,我们痛恨所有非爱尔兰人,或者所有不是警察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警察——无论你是犹太人、黑人、亚洲人或女人——而当你一旦跨进来,加入这个被称为“警察”的种族,你就不得不去憎恨其他种族的人。
以下的数据和文件记录,是在过去的四星期中,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的。我得再说声抱歉,因为文件中的时态可能不太一致(这很难避免,因为写的是一个很近的死亡案件),出现的对白可能不太文雅。我想,我还应该为结局而致歉。我很抱歉,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对我而言,事情是在三月四日那天晚上开始的,然后一天一天开展。我打算就用这种方式来说这件事。
三月四日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在家,我的男人托比参加某个计算机大会,出城去了。我还没吃晚餐,独自坐在沙发上,伴随我的是“小组讨论”笔记以及身边的一个烟灰缸。当时是晚上八点十五分。我之所以清楚记得这个时间,是因为刚好有一班夜车经过,把我从瞌睡中惊醒。夜车那天来得早了些,每逢星期天总是如此。它摇动我脚下的地板,也让我的房租向下直直滑落。
电话铃声响起。打电话来的人是约翰尼·麦克,或称约翰·麦克堤奇警官。他是我在凶案组的同僚,一直担任小队长职务。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好警官。
“迈克?”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大案子。”
我说,好啊,说下去吧。
“这是件很糟糕的案子,迈克。我想请你替我去告知一下。”
“告知”的意思是——通知死亡讯息。换句话说,他希望我去告诉某人,说他有某个亲人死掉了。由他的声音我可明显听出,有某个他们喜欢的人死掉了,而且死得突然,死得惨烈。我心想,我当然也可以说:“我不再干这种事了。”(虽然资产没收组其实也很难和尸体脱离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有一段类似电视剧才有的那种狗屁对话内容。他会说你得帮帮我,或迈克,我求你了,而我会说算了吧,门都没有或少做梦了,老兄,直到所有人都听烦了,而最后我还是得答应下来。我的意思是,当你只能说“是”的时候,为什么要说“不”呢?所以我只好再说了一遍:好啊,说下去吧。
“汤姆局长的女儿今天晚上自杀了。”
“珍妮弗?”我脱口而出,“你他妈的鬼扯!”
“我希望我是在鬼扯,迈克。但真的,情况就是这么糟。”
“她怎么自杀的?”
“点二二口径手枪,塞进嘴里的。”
我没吭声,等他继续说下去。
“迈克,我希望你去告知汤姆局长,还有米里亚姆。马上去。”
我又点上一根烟。我已经戒酒了,烟却断不了。我说:“珍妮弗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
“我知道,迈克。所以你懂了吧?如果你不去,那谁去呢?”
“好吧。不过你得先带我去现场。”
我走进浴室上妆,草率得像某个例行公事,擦桌拖地般完成。我瘪嘴看着镜中的脸。以前我可能还有几分姿色,我猜,但现在我只是个大块头的金发老女人。
没有多加思索,我发现自己已带好笔记本、手电筒、橡胶手套,以及我那把点三八短管手枪。
一旦你当上了警察,你很快就得习惯那种我们称之为“是,没错”类型的自杀案件。你打开案发现场的房门,看见尸体,环顾整个房间,然后说:“是,没错。”但是,这次绝对不是那种“是,没错”类型的自杀。珍妮弗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是我喜爱的那种类型之一,也同时得到所有其他人的宠爱。我看着她长大,愈来愈亮丽、愈来愈美艳,完美到令人不知所措的地步。的确,我心想,这是让人愿意为之赴死的亮丽,是让人愿意为之舍命的美艳。这种美丽并不让人觉得压迫,或者说,它仅带有一点点那种亮丽美艳的女人自动散发出来的压迫(无论她们是多么平易近人)。她什么都有,而且不只这样,她所拥有的可以说比别人更多。她的父亲是警察,她那两位年纪大她许多的兄长也是警察,两个都在芝加哥第六区的警局工作。珍妮弗不是警察,她是蒙特利这里的天文学家。至于男人……她随手捻来,要多少有多少,CSU大学就是她的罗曼史基地。但最近——天啊,我不知道——大概有七八年了吧,她一直和那个大脑发达的意中人——特雷弗·福克纳教授——同居。这绝对不是一个“是,没错”的自杀案件,这是一个“不,有问题”的自杀案件。
我和约翰尼·麦克共乘一辆没有警徽标志的侦防车来到现场。这里是惠特曼大道,各式独栋或半独栋的住宅,林立在宽阔的林荫道路两旁。在二十七街边有一栋学院宿舍,我在这里下了车,身穿运动裤,脚蹬轻便鞋。
照例,现场来了好多警车和警察。鉴识人员和法医也来了,还有托尼·西尔维亚和奥坦·欧伯伊,他们全在屋子里。现场还有一些邻居,都是来围观的,完全不必加以理会。警车车顶警示灯光芒闪耀,穿制服的警察在灯光下穿梭,我知道他们全被调来为这突发的重要案件奔走。在南区也一样,你只要按下无线电开关说有警察倒了,就会出现同样的景象。倒了这字眼,通常表示大麻烦,有时在一场追逐后倒在某个复杂巷弄,有时倒在某个仓库地板,或双手蒙眼倒在某个已人去楼空的偏僻毒品交易场所。每当有人发现有警察遇害后,所有人都会为了这位遇难的警察超时工作,并且用上种种特殊手段。因为这是属于种族的事,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攻击。
我亮出警徽,在大门前的重重穿制服的警察中开出一条通道。今晚的月亮很圆,反射出的太阳光芒落在我的背上。即使是最多情的意大利警察,也不会在这种时刻咏叹月圆,你的眼光只会落在那超时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工作量上。一个周末月圆之夜,而我们只能在急诊室轮班守候,注视在外伤中心进进出出的人们。
在珍妮弗公寓的房门口,我遇到了西尔维亚。西尔维亚曾经和我合作过很多案子,我们就像这样,一起站在许多突逢巨变的家庭中。不对,这次完全不一样。
“天啊,迈克。”
“她在哪里?”
“卧室。”
“你看完了?等等,别告诉我。我自己进去。”
珍妮弗的卧室就在客厅旁边,我知道该怎么走,因为我曾经来过这里。这些年我可能来过十几趟,有时替汤姆局长带点什么东西过来,有时是载珍妮弗去参加球赛、沙滩派对,或是部长的某个宴会。除她以外,特雷弗也曾经顺道搭过一两次便车。尽管这是一种因职务而建立起的友谊关系,但我们每次在车上都很有话聊。我走过客厅,来到卧室门边时,脑海突然闪过一个画面。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在奥弗玛斯警司装潢完工后举办的宴会上,我看见珍妮弗从她捧了一整晚的白酒杯上抬头,对我微微一笑(那时除了我以外,几乎所有人都醉了)。当时我想,她真是个容易快乐的人啊,更是上天的宠儿。我至少需要一百万吨的威士忌,才有办法让自己燃烧起来,绽放出她仅需半杯白酒下肚就能释放出来的那种令人神魂颠倒的风采。
我走进房间,将房门带上。
照程序,是应该这么做的:你必须以绕圈的方式缓缓进入现场,从最外围开始,最后才是陈尸处。别误会,我当然知道她在哪里,尽管我的直觉是在床上,但她其实是坐在一张椅子里。那张椅子就在房间的角落,在我的右手边。除此之外,房间里还有半掩着遮去了一半月光的窗帘、有条不紊的化妆台、蓬蓬乱乱的床单,以及一种淡淡的属于肉欲的气味。在她脚边,有一个破旧的黑色枕头套,另外还有一罐303清洁喷雾剂。
我说过,我早已习惯与尸体为伍,但当我看见珍妮弗·罗克韦尔时,仍不免全身发热。她全身赤裸地坐在椅子上,嘴巴张着,眼睛仍水汪汪的,脸上带着一种天真的惊讶表情。这个惊讶很轻微,一点也不夸张,就像在不经意中突然发现某个早已遗忘的东西似的。话说回来,其实她并不是全裸。噢,天啊,她动手的时候是用毛巾裹着头的,就像你洗完头打算吹干之前的样子。当然,现在那条毛巾已经湿透了,变得完全血红,看起来沉甸甸的,似乎重得让任何活着的女人都无法支撑。
不,我没有碰她。我只是专心记我的笔记,画我的现场素描,完全从专业的角度——仿佛我又被调回了凶案组。那把点二二手枪屁股朝上侧向一边,抵住一只椅脚。在离开房间之前,我用戴着手套的手把灯关掉了一会儿,看着她的眼睛在月光底下闪闪发亮。刑案现场就像报纸上的图案智力测验,观察差异,你就会发现错误。珍妮弗的胴体美极了,无法想象竟然会有人的身体可以像这样,然而,这之中却有件事情不对——这个胴体是死的。
西尔维亚走进来,将凶器装进了袋子里。然后刑事鉴识组的技师会来采指纹、测量距离、拍摄许多相片。接着法医会过来,把她推走。最后,就是宣布她死亡的时候了。
关于女警的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在于她们是否能胜任工作,或是她们究竟能撑多久。换个说法,也许是我个人的问题——说不定我正是那种拖垮其他人的笨蛋。举例说吧,在纽约市警局,女警人数就占了百分之十五,而全国各地的女性警探也屡有亮眼表现,干得有声有色。可是,我总觉得这些人是非常、非常杰出的女性。当我自己在凶案组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放手做吧,没人可以阻挡得了你,大胆去做就对了。调查谋杀案是男人的工作。男人犯下凶案,事后由男人来收拾残局,由男人来破案,而后再由男人来审判。因为男人天生喜欢暴力。女人和凶杀案真的扯不上边,除非是当被害人,或是死者家属,当然,还有扮演目击者的角色。我记得十几年前,在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快结束前所进行的军备扩张时期,当时所有人都挂念核武器的问题,而那时我也觉得那场最终的大谋杀就快来临了。我想象会有一天,我收到勤务调度员的呼叫,告知我有五十亿名死者的事:“全都死光了,除了你和我。”光天化日下,男人都坐在桌前,意识清楚地策划各种可以杀掉所有人的草案计划。我大声询问:“那么女人呢?她们都上哪去了?”女人那时候上哪去?我来告诉你:她们都变成了目击者。那些排列在英国格林汉康芒格林汉康芒,为冷战时期北约部署核武器之空军基地。1982年曾有妇女团体在此发动和平示威,以三万个女人手拉手形成长达九公里的人链围住此基地。
的帐篷外,以出席和怒视让那些军人为之疯狂的姑娘们——她们就是目击者。理所当然,关于核武器的部署与使用,完全都是男人的事。谋杀是一种男性的作为。
不过,倒是有一件与谋杀案相关的工作,由女性来做会比男性好上一千倍,那就是传达通知——关于消息的传送散播,女人可以说是个中好手。男人总是把这种事情搞砸,因为他们处理情绪的方式向来如此。他们总是把通告死亡当成一种任务,于是他们会变得像个牧师、像个街头公告员,或麻木恍神地有如在朗读期货交易单或保龄球计分表。然后,直到中途,他们才忽然觉醒他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事,但那时的事情可以说差不多已砸锅了。我就曾亲眼见过,有位巡警在某个可怜人面前大笑出声,此人的妻子才刚惨死在货柜车的车轮底下。直到这种时刻,男人才明白他们的不胜任,但一切都来不及改变了。相对而言,我敢说女人能立即感觉出事情的轻重,虽然这种事的困难度仍在,却还不至于无法处理。当然,有时候他们会突然大笑出声——我说的是那些被当成死者家属的人。当你正要开始例行的“我很难过传达此消息”的任务时,他们却在凌晨三点吵醒隔壁邻居,要他们加入这场派对。
但是,这种事今晚并不会发生。
罗克韦尔家位于西北郊区,从布莱克索恩出去约二十分钟的车程。我让约翰·麦克堤奇留在车上,自己则像以前来访时那样,绕过屋子向后门走去。当我走到屋子侧面时,我暂时停下脚步,为的是踩灭香烟,深吸几口气。此时,穿过那扇玻璃窗、穿过厨房的那些盆栽,我看见了米里亚姆和汤姆局长。他们正翩翩起舞,在荡人心弦的萨克斯风音乐下,忘情地扭转摇摆。他们还举杯互敬,杯中盛着的是醇美的红酒。天上,圆满的月亮在云朵中穿梭露脸,仿佛那些云朵是属于月球的,而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东西。没错,这是一个美到令人难以忘怀的夜晚,而这种美丽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像是刻意为我设计的,在这幅镶在厨房窗户上的图画中,我看到的是:一段四十年的婚姻,竟然还他妈的存有爱意在里面。就在这个月光映照有如白天的甜美夜晚。
若你像我此时一样,身上带了这种不幸的消息时,你的身体就会产生特别的反应。它会感觉到一种凝聚力,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它会感觉到力量,因为它带在身上的是一个强大无比的事实。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描述,但事实却是不容质疑的。事实就是事实。事实就是这样。
我轻敲有半面玻璃的后门。
汤姆局长说,很高兴看到我。他眉头皱也没皱,没有一丝的不悦,完全没怪罪我跑来让这个夜晚黯然失色。但是,就在他把门打开的刹那,我就感觉自己的脸垮下来了。我知道他会怎么想,他一定以为我又故态复萌了。我说的当然是指酗酒。
“迈克?天啊,迈克,你没事吧?”
我说:“汤姆局长?米里亚姆?”但米里亚姆已经逃开了,以三十二英尺每平方秒此为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的速度离开了我的视线。“你女儿没了,今天发生的。你失去珍妮弗了。”
他看起来像在努力保持微笑,似乎笑容能把这件事化解掉,但微笑却转而变成否认。那年他们生了戴维,来年生了乔舒亚。然后,隔了十五年,他们才有了珍妮弗。
“真的,她真的走了,”我说,“是她自己下的手。”
“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