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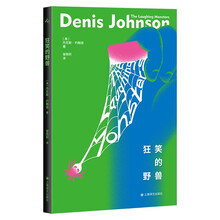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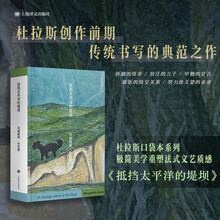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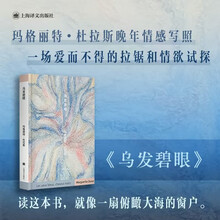





《贺拉斯》样章试读:
我们最爱的人往往不是我们最敬重的人。爱不需要钦佩、热情,它建立在感情平等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在寻找朋友的时候,总要找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有着共同的爱憎喜恶,弱点相同。而敬重需要的是另一种感情,它有别于友谊——时时刻刻亲密无间的感情被称为友谊。有些人不爱他敬重的人,我对这种人没有好感;有些人则只能爱他敬重的人,对这种人我更没有好感。这也只是就友谊而言,男女间的情爱又当别论,它只靠热情维持生命,伤害了它的敏感微妙之处,爱情之花便会枯萎凋谢。但是人类所有感情中最美好的,在患难与共中、在错误挫折中、在伟大事业中、在英雄行为中结交的感情,伴随我们一生各年龄阶段的感情,与人的第一感情一起在我们内心激生的感情,与我们的生命同在的、使我们的生命价值倍增、能使我们的生命不朽的感情,能够死灰复燃、破镜重圆且与往日一样紧密牢固的感情,这样的感情,唉,并非爱情,你们知道,这是友谊啊。
如果我在这里大谈我对友谊的感受和认识,我会忘记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会写一大本不知有多少卷的论著,但恐怕找不到几个肯读它的读者。在我们这个时代,友谊已不时兴。人们已不再追求友谊,只需要爱情。因此,我只限于讲以上的话,作为这故事的开场白。我有一个朋友,是令我最感惋惜的一个人。他与我一辈子都有交往,他不是完美的人、最善良的人,恰恰相反,是个缺点不少、有怪癖的年轻人。有些时候我甚至蔑视他、恨他。可是我却对他有极其强烈的、不可抑制的感情。
他的名字叫作贺拉斯·杜蒙特,是外省一个月薪一千五百法郎的小职员的儿子。小职员娶了一个有钱的乡下姑娘,继承遗产达1万埃居。就如人家说的从天上掉下三千法郎年金。小职员的前程,也就是他的晋升,是以他的工作、健康、品行为抵押品的,需要他能盲目地赞同某政府、某团体的所有法规条文。
我这位朋友的父母杜蒙特先生与夫人,眼见自家的社会地位不牢靠,经济不宽裕,决定送他们的儿子接受所谓的教育,也就是送他到外省一间中学就读,直至他毕业,再送他到巴黎继续上高等专科的课程,几年之后让他做律师或医生。他们有这样的打算并不奇怪,因为处于同样地位的家庭无不做这类野心勃勃的梦:让他们的儿子过独立生活。“独立”所表示的意思便是可怜的小职员的理想。他们饱受节衣缩食之窘,唉,还经常忍受屈辱,当然希望子孙后代能摆脱这样的命运。他还以为四周有的是向他抛下来的各种彩票,锦绣前程俯拾即是呢。人往高处走,幸亏人类有此本能,因此,脆弱的、不平等的社会大厦得以支撑,没有坍塌下来。
要摆脱贫困卑微,在能够选择的范围内,今天的家长不会为孩子挑选虽可靠但低微的职业。首先要满足的是贪心与虚荣心。周围不是有困龙得水,拨云见日的例子吗?他们不是亲眼见到底层的天才、庸才爬上社会顶层吗?杜蒙特对妻子说:“我们的贺拉斯难道就不能像某某等许多才干与胆识都不如他的人那样获得成功吗?”
杜蒙特夫人听见丈夫要她为儿子的飞黄腾达做出牺牲有点吃惊。但世上有哪一个母亲不以为自己生了一个最聪明、得到上天恩宠最多的孩子呢?杜蒙特夫人是个头脑简单的善良女人,在乡下长大,她的见识被她所受的教育局限,除了她熟识的生活圈子之外,还有个陌生的世界,她只能以丈夫的眼光去观察。她丈夫对她说,自从大革命以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没有阶级偏见了,凡有才华者均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闯出一条路抵达目的地,只不过需要使一点劲儿推开靠近目标的人。她认同这些道理,她不甘被人看轻,被视为落后的顽固分子。这方面与她农家出身一致。
杜蒙特希望她做出的牺牲,就是交出不少于一半的收入。他说:“有一千五百法郎,我们和身边的女儿尽可以凑合着过日子,余下的钱加上我的薪金,便够供贺拉斯到巴黎宽裕地过上几年了。”
拿出一千五百法郎给十九岁的贺拉斯·杜蒙特在巴黎过好日子!杜蒙特夫人不惜做出任何牺牲,可敬的妇人为了有利于儿子的前程,为了取悦丈夫,甘愿啃黑面包、光脚板,但要她一下子倾尽出嫁以后高达一万多法郎的积蓄,她不免有些心疼。那些不了解外省人过小日子的人,不了解一个主妇的持家本领,她节衣缩食,锱铢必较,从每年的三千法郎年金里硬是省出几百埃居来,而又让丈夫、孩子、仆人、猫不致挨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亲身经历过这样生活的人则见惯不惊。一个没有才能、没有本事、没有财产、没有其他办法维持家计的女人,只能使用节流的方法,在日常的生活开支上削减,克扣一点必需品。这种生活当然是凄凉暗淡的,缺乏欢乐、不公道的,单调乏味的,连宴请客人也办不到的。富人们却认为这种现象算不了什么,社会财富分配很合理!谈到小资产阶级时,他们说:“就让他们勒紧裤腰带去培养子女好了。不想勒紧裤腰带,那就让他们的子女做手艺人、泥水匠为我们效劳吧。”从社会的权利角度看,富人的论调倒有点道理,若论人权,唯有上帝才能判断了。
穷人会在他们简陋的住房里发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与工业巨子等高贵老爷的孩子平起平坐?受教育应是人人平等的。上帝要我们为消灭贫富的差距而奋斗。”
正直的人们,总之,你们的话也有道理,而且永远正确。尽管你们的希望常常化为泡影。可以肯定,我们还要长期沿着合法的野心、天真的虚荣心这条道路,向平等这个目标走去。不过,有朝一日,当权利和机会实现均等,当所有人在社会上都获得应有的地位,所有人的生活不但衣食无忧而且富余,我们完全可以指望,每个人在自由平等的气氛中,更理智更谦虚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心浮气躁地,在激烈竞争的气氛里过高估计自己。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天终会来临——青年们不再野心勃勃,头脑发热,非要成为时代的头号人物不可,或不成功则成仁。到了这一天,每个人都享有政治权利,行使这些权利被视为每个公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到那时,人们不会像今人一样,热衷功名,在仕途上死命钻营,狂热地追逐权力。
杜蒙特夫人原打算把她的一万多法郎的积蓄作为女儿的妆奁,如今同意动用这笔款子供儿子到巴黎读书。日后又得省吃俭用,积一笔钱送贺拉斯的妹妹卡米尔出阁了。
就这样,揣着一千五百法郎的学费,十九岁的中学毕业生贺拉斯出现在巴黎的繁华街头,成了一名法学院的学生。我在靠近卢森堡公园的小咖啡馆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在巴黎学习了或算是学习了一年。每天早晨我们在这家咖啡馆喝咖啡、读报纸。他彬彬有礼的言谈举止,开朗的神气,机灵温和的目光,一见面便赢得了我的好感。年轻人相遇很快便能成为朋友,只要一连几天坐在同一张桌子边,讲几句客套话,到了阳光灿烂的早晨,他们便会交谈起来,海阔天空地畅谈,从咖啡馆一直走到卢森堡公园的小径深处。这就是一个春意撩人的早晨我与贺拉斯交往的情况。丁香花正在盛开,阳光欢乐地照耀在咖啡馆美丽的老板娘普瓦松太太那张镶了黄铜的桃木柜台上。我与贺拉斯不知不觉走到公园的水池旁边,彼此挽着手臂,就如一对相识已久的老朋友,而我们还不知道对方的姓名。诚然,促膝谈心,交换对一般事物的看法,使我们的心突然贴近了,但还是摆脱不了矜持的态度,却增加了我们这两个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信任。这一天,我仅仅知道贺拉斯学的是法律,他也仅仅知道我是医科大学生。他向我提的问题局限于我对自己攻读的学科的看法,我亦如此。
两人分手时,他对我说:“我佩服你,或者应该说,我羡慕你,你在努力学习,不浪费光阴,你热爱科学,你有希望,朝着目标勇往直前!而我呢,我走的路与你的不同,我不愿坚持走下去,我只想摆脱它,我厌恶法律是有道理的,满纸谎言,违反上天的公道,违背永恒的真理。如果这谎言有逻辑性、系统性倒也罢了,偏偏它又自相矛盾,真是无耻之尤,其目的就是要我们以卑鄙的手段干歹事。如果有哪一个年轻人把这所谓的研究诉讼的歪理当了真,他便是个无耻之人、荒唐的家伙,我就要蔑视他,憎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