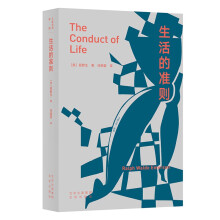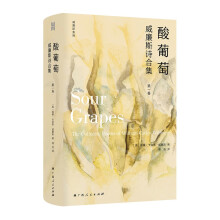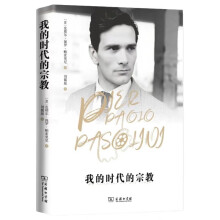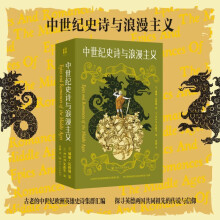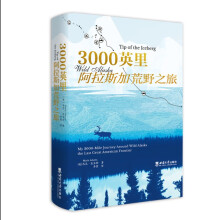《空间叙事与国家认同:格温朵琳·布鲁克斯诗歌研究》:
从主流话语看,欧洲中心的城市衰落话语将黑色麦加塑造为城市溃烂的象征,布鲁克斯则从内部视角展现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麦加居民生活与思想的侵入和压迫,阐述种族主义加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城市的危机,从种族的政治立场与城市衰落话语形成“差异对话”。在叙事技巧上,诗人采用了“含糊不清”的言说方式,黑人住户通过帕蒂塔将个人痛苦和悲怆转为族群共同的精神体验,在与圣灵亲密的认同中黑人住户走出封闭的单个公寓,建立起群体信任与责任,个体讲述汇集成黑人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叙述。布鲁克斯以诗歌形式对麦加内部的生存状况作了客观性的报道,与官方舆论形成了反话语。从次主流话语看,民族主义主导的黑人权力运动话语瓦解了白人霸权对麦加空间的禁锢,开启了黑人意识重燃的替换性空间。布鲁克斯在认同民族主义政治立场的基础上,以“杂语”的叙事技巧赋予个体与特定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紧密相连的独立声音,在民族存亡的公共话语领域呈现了族群内部多样化的社会层次构成。同时,诗人从性属的视角,通过帕蒂塔对自身遭遇的重述,打破了黑人权力运动单一的男性认同话语模式,在“同一辩证”中预示着群体内部建构的变革性力量。因此,诗歌对主流话语与次主流话语产生了断裂和修正,弥合了权力话语所投射的麦加衰落与帕蒂塔悲剧的影像同现实状况之间的裂隙,在对种族之间与种族内部的双重批判与唤醒中,麦加成为反思战后美国城市集体性社会危机的平台。
其次,在艺术形式层面,“言语混杂”转化为艺术思想,贯穿诗歌整体的语言形式与结构形式。布鲁克斯得到了双重文化的滋育,既有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望,也有进行文化对抗和寻根的冲动,还有在黑人内部权力自决中重申女性身份的挣扎,这种剧烈的碰撞和独特的情感经历积淀、转化为丰富的文学想象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叙事优势。具言之,诗歌既保留了欧洲传统形式与标准英语,又增加了黑人表述模式与方言,既未与传统诗学决然割裂,也未与黑人美学全然融合,并且以艺术形式的复杂性唤入了欧洲根源与非洲根源的文化体系,作为深层对抗与对话的架构,充分展现了诗人在不同文化框架和诗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话”与“同一辩证”。形式结构本身蕴含着社会矛盾,“言语混杂”的艺术理念打破了形式与内容对立的固有模式,为社会的矛盾性危机进入审美领域提供了中介机制。在情节结构上,寻找帕蒂塔与黑人住户个体讲述的两条线索交替出现,以黑人女性多重声音和多种语言的叙事模式推进两条线索在相互参照中并行发展。黑人住户叙述的心理时间打破了寻找帕蒂塔的物理时间,个体经历的封闭空间嵌入麦加整体的压迫性空间。因此,诗歌以对话性结构、非线性时间和碎片化空间等后现代叙事风格,对传统体裁形式产生了断裂与修正,使主题的探讨更具开放性和辩证性。因此,“言语混杂”的麦加重叙打破了文化框架、诗歌形式、诗学传统等对艺术疆界的限制,对麦加在现代性中陨落的社会现实实行了艺术审美的补偿和修复。
此时回到诗歌第二部分题词,全诗的整体寓意和主题思想昭然若揭:“现在麦加道路的事记在下面。”“麦加”不仅是种族主义官方话语压制下黑人的沦落之地,亦是民族主义黑人权力话语激发下黑人的觉醒之地,故而在整体寓意上成为真正的救赎之地,而诗歌记载的正是救赎“道路”的探寻。布鲁克斯以黑人贫民窟麦加为原型,解析和批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衰败,但在深层意义上,却从黑人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经历触及了人性价值与艺术审美在现代性中殒落的问题。黑人女孩帕蒂塔在自我受难与牺牲中传递了悲悯与宽恕,依靠人的本质力量回归到人性的完整,而肉体的残破与消亡经由审美超越了经验世界,在彼岸的艺术世界中获得新生。可见,布鲁克斯将救赎的希望置于人性的力量上,试图唤醒社会给予生命权和人权超越种族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敬重。因此,在麦加荒芜、冷漠、混沌的表象下,诗人始终追寻着一条通往人性、正义、秩序的救赎之路,寄托着对“异托邦”远景的呼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