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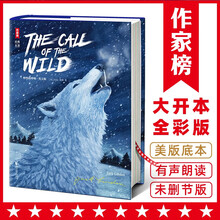



★ “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处女作
★ 获得意大利文坛重磅奖项艾尔莎·莫兰黛奖
★ 改编电影《烦人的爱》(1995)入围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
★ 黛莉亚-阿玛利娅的母女关系,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隐秘源头
就在几个月前(五六个月前?),我回母亲这里,忽然心血来潮地对她说,我十几岁时经常躲避在电梯里,并把她带到了顶楼。也许我希望和她建立一种亲密关系,那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的。也许我当时很迷乱,想让她知道,我一直都不快乐。但她似乎觉得这样很好笑:悬在空中,站在摇摇欲坠的电梯里。
“这么多年来,你有过男人吗?”我在电梯里直截了当地问她。我的意思是:离开我父亲后,她有没有过情人?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是我从小就想问的问题。她坐在离我几厘米远的木凳上,没表现出任何窘迫,连声音都没有一丝异样。她坚定而清晰地说:“没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在撒谎,因此毫无疑问:她在撒谎。
“你肯定有过情人。”我冷冷地说。
她素来很克制,但那次她的反应有些夸张。她把裙子拉起来,一直到腰部,露出松松垮垮、粉红色的高腰内裤。她哈哈笑了起来,说到了赘肉、松弛的腹部,诸如此类的话。她还重复着:“你摸摸这里。”并试图拉着我的手,让我摸她苍白肿胀的腹部。我的手缩了回来,放在心脏上。我的心跳很快,想平息一下。她放下了裙摆,但腿还露在外面,在电梯的灯光下有些发黄。我很后悔把她带到我的藏身之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她能盖住自己的腿。“出去!”我说。她真的出去了,她从来不会对我说“不”。她一步跨过了敞开的电梯门,很快消失在黑暗中。我一个人待在电梯里,感到一种平静的快乐。我不加思索地关上了门,几秒钟后,电梯里的灯光熄灭了。
“黛莉亚。”我母亲小声叫了我的名字,但没有惊慌失措。在我面前她从不惊慌,在当时的情况下,出于一种老习惯,她不是在寻求安心,而是试图让我安心。
我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品味着她呼唤我名字时的声音,那就像记忆里的回声,在脑子里回荡,是一种无法捕捉的声音。我觉得那像在遥远的记忆里,她在屋里找我,找不到时,呼唤我的声音。
现在我就站在电梯里,试图消除对那个回声的记忆。但我感觉,我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有人在监视着我。那不是几个月前的阿玛利娅,她已经死了,而是“我”走到了电梯外面,看着自己坐在那里。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痛恨自己,我看到自己默默站在一部破旧、黑漆漆的电梯里,电梯悬在空中,钢索疲惫地垂在下面。我就像藏在树枝上的鸟窝里,这让我有些羞愧。我把手伸向了门,摸索了一阵子才找到了把手,我打开门,带花纹的玻璃后面的黑暗消失了。
我一直都知道,我想到阿玛利娅时,有一条无法跨越的界限,也许我去那里,就是为了跨越它。我感到害怕,我按了去三楼的按钮,电梯摇晃了一下,发出很大的声响,吱吱扭扭地下行,最后停到我母亲住的那一层。
4
我向邻居德利索寡妇要了我母亲的钥匙。她把钥匙给了我,但坚决拒绝和我一起进屋。她肥胖而多疑,右脸颊上有一颗很大的痣,上面有两根长长的灰毛。她的头发分成两股,胡乱扎成两条辫子。她穿着黑色的衣服,也许那是日常穿的,也许她还穿着参加葬礼的衣服。她站在门口,看着我在试探,找那把能打开门的钥匙,但门并没锁好。一反往常的是:阿玛利娅只锁上了两道锁中的一道——钥匙只需转两圈的锁,她没锁上另一道锁,那是一道钥匙需要转五圈的保险锁。
“为什么呢?”我打开了门,问身边的邻居。
德利索寡妇犹豫了一下说:“她有些魂不守舍。”但她觉得,这样说可能有些不敬,就补充说:“她很高兴。”她又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她本来很乐意说些我母亲的闲话,但害怕我母亲的鬼魂在楼梯间、公寓里,当然还怕在她的房子里徘徊。我再次邀请她进来,希望她能陪我说说话,但她打着哆嗦、红着眼睛坚决拒绝了。
“她为什么高兴?”我问。
她又犹豫了一下,下定了决心。
“一段时间以来,有位身材高大、很体面的先生经常来拜访她……”
我充满敌意地盯着她,决定不让她继续说下去。
“那是她哥哥。”我说。
德利索眯起眼睛,显然有些生气:她和我母亲是朋友,认识很长时间了。她跟菲利波舅舅也很熟悉:他既不高大,也不体面。
“她哥哥。”她假装同意我的话,一字一句地说。
“不是吗?”我问。她的语气让我有些烦。她冷冰冰地向我打了个招呼,关上了门。
进入刚刚去世的人的屋子,你很难相信它是空的。屋子里没有鬼魂,但确实保存着生命最后几天留下的痕迹。我先是听到厨房里传来急促的水声,有那么一刹那,现实和幻觉交替出现,我有些恍惚。我觉得我母亲没有死,她的死亡只是一场漫长、痛苦的幻觉。我不知道这种充满焦虑的想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确信她还活着,她在屋子里,站在水槽前一边洗着碗,一边自言自语。但百叶窗关着,公寓里一片漆黑,我打开灯,看到老式铜质水龙头开着,水哗哗流入空荡荡的水槽。我关上了水龙头。我母亲属于坚决反对浪费的老一辈人,她从不扔掉干面包,奶酪皮也不扔,也会放在汤里煮,给汤提味。她几乎从不买肉,而是向屠夫要他们剔过的骨头来做汤,她吸食骨髓,就好像它们含有神奇的养分。她用水极节约,她的动作、耳朵、声音都形成了一种自然反应。她永远不会忘记关水龙头,我小时候如果没把水龙头关好,如果有一丝水流向水槽底部,就会留下一摊硬币大小的水痕,过不了一会儿,她就会朝我大喊:“黛莉亚,水龙头!”她的语气里并没有责备。她生命最后几个小时不小心浪费的水,比她一辈子浪费的还要多,这让我感到很不安。我看到她脸朝下,漂浮在那里,悬浮在厨房中间,在蓝色瓷砖的背景中。
我很快去了另一个房间。我在卧室里走来走去,用塑料袋收集她一直保留着的几样东西:家里的相册、一只手镯、一件五十年代做的旧冬装,我很喜欢。其余的都是连收破烂的人都不会要的东西:几件又旧又丑的家具。她的床只有床架和床垫,没有靠背,床单和被子上有很多补丁,考虑到它们的年代,简直不值得去缝补。让我觉得惊异的是:她平时放内衣的抽屉是空的。我在放脏衣服的袋子里找,发现里面只有一件质量考究的男式衬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