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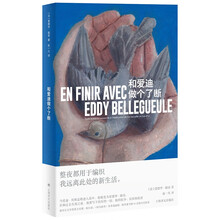
丛林猛兽
在他们不期而遇的这段时间里,究竟是什么引发了那么一段使他愕然的对话?也许是在他们再续前缘后闲庭漫步时,自己口中无意间蹦出的一些话?但这一点儿也不重要了。就在一两个小时之前,几个朋友领着他来到了她所在的这间屋子,还有一部分访客则前去参加午宴了。他其实也是众多来访者之一,不过,在他看来,多亏有那乌泱泱的一群人,自己才能一如既往地被湮没在人群中。午饭过后,人们陆陆续续散开了,他们本意就是来看看韦瑟恩德庄园的景致,来欣赏绘画、传家宝、艺术瑰宝等特色藏品的。这些珍品使得韦瑟恩德庄园颇有了些小名气。这里有数不清的宽敞、气派的房间,所以访客们可以离开人群,自己随意闲逛;当需要长时间认真思考时,那些宽大的房间也能让他们沉醉在故弄玄虚的鉴赏和品评中。总有一些人——要么独自一人,要么成双结对——在弯着腰检视某些偏僻角落里的展品,手掌撑在膝盖上,他们一个劲儿地直点头,仿佛是在证明自己捕捉到了某种令人兴奋的气息。当两个人凑在一起时,他们那貌似心醉神迷的讨论声便交织在一起,但也有可能两人同时陷入了更具意蕴的沉思之中。在马切尔看来,此情此景简直就像过度炒作的大促销的前夕,既可激发起人们的占有欲,也能迅速浇灭这股热情。在韦瑟恩德庄园,占有欲者的美梦应当是、也的确是狂热不羁的;约翰?马切尔置身其中,只觉得自己既为那些太懂行的访客担忧不已,又替那些不懂行的捏一把汗。一个个宽敞的大房间使他脑海中涌入了许多诗歌和历史典故,他需要避开人群闲逛一会儿,好让自己更真切地去感受它们;他那么做时,并不像某些同伴那样一脸的贪婪,活像一只正在嗅闻橱柜的狗,但也就在他那么做时,事情立马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
简而言之,在这个十月的午后,他那么做使自己与梅?巴特拉姆以更亲密的方式相遇了。他们远远地分坐在一张很长的桌子旁边;她的脸似曾相识,然而他无法搜寻到那段记忆。这张面孔使他略感不安,却又是一种夹杂着愉悦的不安。他能感知到这张面孔会成为某种东西的延续——某种他已遗失了开端的东西;而在那一刻,他也乐于接受这种延续。他不清楚它延续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这样也很耐人寻味,或者说,不失为一桩乐事。更重要的是,即使她没有明确传达出什么信号,他也多少意识到了一件事,那便是,这位年轻的女士并未丢失线索。她没有忘却与他的过往,但如果他不主动出击,对方也不会告诉他。他不仅看到了这一点,还看出了别的一些更奇怪的事:一次又一次巧合使他们再次面对面相遇了,但他暗自琢磨后,依然觉得他们之间的过往无关紧要,可如果那些过往真的无足轻重,那么为何他又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她的分量呢?他的答案却是:生活在这样的尘世里,人们只能走马观花,随遇而安,于是乎,他俩便暂时突然显得重要起来。尽管他完全说不出为什么,但却满足于认为这名年轻女士大概是这屋子主人的穷亲戚;也满足于认定她并非只是在这儿做短暂的停留,而多少算该家族中有工作、有薪酬的一员。她应该享有定期的保障吧?所以,她应该是为了回报这一待遇才来这儿的,除了提供别的一些服务外,还帮忙导游和解说,跟无聊的人打交道,解答关于这栋建筑的落成日期、家具风格、绘画作者、鬼魂经常出没的灵异之所等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她看上去像个会接受施舍的人——虽然看似不太像,但也不是不可能。当她终于款步走向马切尔时,即便比他以前见到她时老了许多,仍然显得格外端庄。她觉得在这几个小时里,马切尔投在她身上的注意力比投在其他所有事物上的加起来都要多,因此,他悟出了某种别人因迟钝而无法猜透的真理——但这也只是她的猜测而已。她的确过得比这儿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艰难;之所以出现在这里,也是近几年遭受了种种困苦的缘故。她还清楚地记得他,就像他也记得她一样,只不过她记得更加深刻而已。
他们的朋友都离开了这个房间,只剩下他俩,两人站在壁炉前的画面,好似一幅精美的肖像画。终于,他们开始交谈了。此时此刻的美妙之处在于,早在开口之前,他们就像彼此早已约定好了似的,要留下来谈一谈;令人愉悦的是,其它事物也显得十分美妙,部分原因是由于韦瑟恩德庄园几乎处处都值得留恋一番。美妙之处就在于,秋日白昼那渐渐褪去的光辉穿过高高的窗户透进屋子里;美妙之处还在于,红光突破那低矮、阴沉的天空,射出一道长长的光柱,掠过那陈旧的墙板和挂毯,掠过那古老的金饰与染料;美妙之处也许更在于她来到他身边的方式。她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与他单独相处的方式,因此,如果他能低调行事、不自作多情的话,她对他的那点儿微不足道的关注,也许不过是她一贯的待人方式而已。然而,当他听见她的说话声时,缺口却被填满了,那遗失的一环也连结上了;他从她的态度中嗅到的那一丝嘲弄的味道,也就此失去了锋芒。为了抢在她之前抓住话头,他近乎唐突地直击主题:“很多年前,我曾在罗马见过你。我还记得那时的一切。”她承认,自己的确有些失望——她本以为他肯定忘记了;为了证明自己记得有多清楚,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许多详细的片段,这些片段都是他重拾记忆时突然冒出来的。此刻,她的神色、她的声音都由他来牵动,产生了奇妙的效果——它们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如同灯夫手里的引火棒,一触即燃,仿佛在一盏接一盏地点亮长长的一排煤气灯。马切尔颇为得意,自认为自己的这“灯火”点得“足够亮”。她被逗乐了,便告诉他,就在他急于证明自己确切地记得每一件事时,已经把大部分事情都记岔了——但他乐于听她纠正这些错误。比如,他们不是在罗马相遇的,而是在那不勒斯 ;比如,那时并不是七年前,而是将近十年前;比如,她那时并不是与叔叔婶婶结伴,而是与母亲和哥哥在一起。此外,令他颇有点儿困惑的,是她有证有据地力争的一点——他当时并未与潘勃尔一家同行,而是与布瓦耶一家一同从罗马过来的。她虽然听说过潘勃尔家族,却不了解他们,而布瓦耶家族,她倒是清楚的。也正是和他同行的布瓦耶家的人,使得他们认识了彼此。当时,一场意外的雷雨袭来,肆虐无比,逼得他们逃到一个正在施工的坑道里——这场意外不是在凯撒宫发生的,而是在庞贝古城,当时他们是为了参观一个重大发现才到那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