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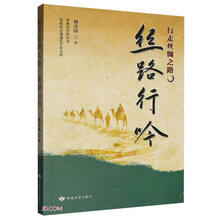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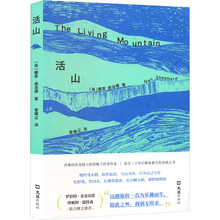



※ 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构不成什么重要的意义。可它们就是回荡萦绕,对他轻声细语,成为照亮生命的星。他写作的对象就是那些星星:贾植芳、海子、柏桦;扬州慢、鹊桥仙、蓬莱清浅;还有北京的秋叶……通过文字,作者将它们从时光深处召唤出来。
※ 一种隔着时间距离的在场感。2005年,他见贾植芳,感受这位老人一生的激荡、潇洒与磨难仿佛都收拢在一根拐杖的拐角;2008年,参与文学奖现场,看见贾平凹、迟子建、周大新、麦家……写作对象带给他的触动,并非仅仅通过文字,也来自眼见与日常。
※ 作者行文如家乡北方温榆河畔的秋色,干净、干脆,稳得住超拔,接得住苍凉,潜藏着开阔而丰饶的诗性。
冷魂贾植芳
2002年,李欧梵拜见施蛰存,提出庆贺他百年寿辰,施先生答道:“我是在等死,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此语初闻,震撼无以言表。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巴金,如今巴老已然在彼地历经一两个驿站。
“驿站”的说法来自贾植芳先生。贾先生初见我这个后生便说:“这些年我看到最多的是讣告。”在一篇文字里他写得更加详尽:“我也常常到火葬场去参加告别仪式,每逢这种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对墙上用黑边围绕的死者遗像低头默哀。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而今,四月春风别冷魂。
2005年9月,我曾为复旦百年庆典拜访老人。贾老已然九旬。其实我第一次见到老人时,他业已八旬上下。世事如此,有些人我们甫闻其名,他便绝然离去,譬如海子;有些人我们初阅其文,他便垂垂老矣,譬如夏志清。
老人黑鞋白袜灰裤子,白衬衣里白背心,鼻子很挺头发灰白。贾老和侄女任桂芙一家同住,四世同堂。整个宿舍区静极,与那个正在全身麻醉、通体手术的复旦截然两个世界,尽管离得那么近,一本书掉下来便几乎落到复旦那边去了。他喝了一口水,道:“我无儿无女……”遥想当年讲坛,瘦小的老头儿谈笑风生,身边还有着一名同声翻译。他的山西口音历经数十载亦不曾被“驯服”。此刻,坦白地讲,老人的话我听不甚清。
适逢一个山西老乡的女儿考取了同济大学,特地来看望老人家。见我到来他们便转而和贾老的侄女聊天,时有笑声。临了家乡人拿出颠簸了几千里的礼物:一兜月饼,是家乡人自做的。贾老接过来看了看,摸出一个递给我道:“吃一个。”这三个字很是清晰。我接过,咬了几口方吃到“馅儿”,甜,却硬得厉害。老人叫侄女拿来一本书,签了名送给他们,目送离去。屋里静了下来,山西口音稍稍清晰些了。他说自己多年没回老家,远道而来的乡亲大多不认识,但就是打心底里高兴。
我将自印的诗歌小集子送给老人,他兴奋地说:“我可有很多写诗的朋友呢。”我问,百年校庆您会参加吗?老人稍作停顿,我1987年就退休了……
他咳一声,起身去厕所,走动时越发显得瘦小。
我又咬了一口月饼,留意到桌子上的《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文艺报》《新民晚报》间,夹杂着余华的《活着》和莫言的《红树林》。
回来时他低声说了几句,可惜我又没听清。他侄女告诉我,过会儿他们要去附近步行街上的咖啡馆坐坐。老人近来戒了烟酒,每天早上8点半起床,晚上10点半睡觉。最后,他又让侄女拿来一本小书——《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纪念集》。老人说:“这本书买不到。你看啊,没版权页也没定价,只印了……”我没听清是多少册,但知道老人将亡妻纪念集视为特殊的礼物,刚才送老乡的就是这本书。老人在书上题写了几个字,称我为“木叶老弟”。
他就问起我的年龄,我说过三十了。他说了两句话:一,“哈,我最好叫你‘小弟’,你比我小了六十岁啊。”同时做了个“六”的手势。真正想说的是下面的话:“三十岁正是有经历也有精力的时候,要好好写。”然后他翻起放在桌上的文集,最后在一篇小说上定格:《人的悲哀》。他说:那是我二十刚出头时写的……
老人继续讲道:“我三十岁时来上海,下火车身上只有八分钱。我当时光头,媳妇梳着小辫儿……但你看啊,可以说这八分钱我六十年也没‘花光’,靠的是人格与本领……”
待老人的话我大半能听清,已到告辞之际。
我拍了一张老人卧室的照片: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于谦的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目光下移,一张双人床,被子叠放在床尾,枕头边放着十来本书,床边一把椅子,椅上是一个白色的尿壶,床头墙壁上以胶带粘着几块旧纸箱板……
老人接待我那间屋子,有好几个书架,其中一个书架伸手便可摸到的那两层上,放着高高低低的药瓶。要取阅背后的书就得先拿开药瓶,即便不取书,老人亦要一日三次像吃饭一样取下药瓶,放回药瓶。
我打量这一切的时候,老人说:“现在写不动了,只是记日记。”最后又说,“我想多活几年,看看这风景……”闻听此言,“寿则多辱”四字一下子堵在我心头,瞬间又消逝了,有一种沧桑变得干净利落……
诗人西川的《一个人老了》写的是另一个情景,但用在这里又出奇地妥帖,连不妥帖之处似乎亦妥帖了。引几行:
……他的骨头
已足够坚硬,撑得起历史,
让后人把不属于他的箴言刻上。
必须惭愧地坦白,此前我没有好生读过贾先生的任何一篇小说,也不曾看过他的理论或翻译作品,只是读过陈思和、张新颖等写的一些相关文字,听过贾老的讲座,并一次次或远或近地看到他在复旦园慢慢、慢慢地走着。困惑的是,为何我对一个人如此缺乏了解,便写下如此多的感受与臆测?
告辞出门。这位老人一生的激荡、潇洒与磨难仿佛都收拢在一根拐杖的拐角——有着纹络,有着光润,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写着一撇一捺。
回首。树摇影动,夜色将至。一楼最里屋有一位老人,过会儿他要去咖啡馆坐坐。
注:“冷魂”为贾先生十几岁时用过的笔名
2005.10,2008.5
辑一
梦——留别这个世纪
北京越来越北,或像皇帝一样被均匀地一刀劈开
死生
辑二
相忘于江湖
烂漫
扬州慢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鹊桥仙
零落一身秋
我醉欲眠卿且去
断续
一星如月
事了拂衣去
隋炀帝因书入梦
雨细未沾衣
蓬莱清浅
明灭
辑三
致
命运
天平上多余的一克
有关顾城
博尔赫斯的自习课
海明威的酒杯
上联
剑气
老夫聊发少年狂
魔岩三杰之夜
一个入侵者的面孔
死神来过了
冷魂贾植芳
群像——一个文学奖的一天
索尔仁尼琴。回来。
辑四
诗人和诗歌
诗歌的品格
通向格律之门
一篇未定稿——关于柏桦,或夏天和汉风
附录
阿乙×木叶:自由即爱与被爱、创造与被创造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