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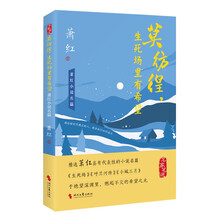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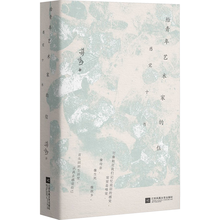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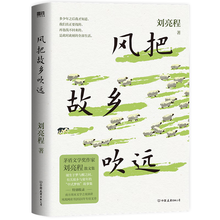
怀念邵燕祥先生
/林贤治
邵燕祥先生离世不觉两年了。
认识邵先生近三十年,在寥落的朋友中,他是我联系最多,感觉最为亲近的一位。邵先生一生追求真知与真理,少年时便倾向革命,即对黑暗的反抗。即使如顾准所说,“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邵先生始终是一个本来意义上的革命者。正当他青春做伴,放歌“到远方去”时,遭逢一场众所周知的打击。然而,他没有停顿,戴着“灰帽子”走向荆棘地。苦难和屈辱不曾摧毁他,反而将他磨炼成为一名“精神界之战士”。这是一名忧郁的战士。虽然,邵先生自比愤怒的蟋蟀、快乐的牛虻,在他激越的歌唱里,毕竟流露着灵魂深处的伤痛。或许,恰如邵先生说的,忧郁本身是一种力量,所以在他面对利维坦,历史的巨灵时,犹能分神于如我一样的后来者,倾注关怀的热情。
无论如何,这是可感念的。
1
中学时代,我迷上诗歌。那时,已经听说邵先生的名字了,就是找不到他的诗集。在学校图书馆,“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著作,全都成了禁书,被锁进几个大木柜里,可望而不可即。
直到“文革”后恢复文艺刊物,我才得见邵先生的诗,至今还记得, 读到那首呼唤高速公路的诗,当时是何等兴奋。那是有时代高度的诗,开阔的诗,乐观主义的诗。但不久,他的诗风便转向沉郁一路了。我刚到省城工作后不久,买到他的诗集《献给历史的情歌》,很是喜欢。那是一个精装本,庄重而美丽。
一九八四年,邵先生在《文学评论》发文提倡“史诗”。我按捺不住,读后立即写信给他,表示不同意见。或许,其中提到的史诗与相关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太复杂,使他感到为难,未见作复,但想不到信被保存下来了,后来由他编入名为《旧信重温》的书中。收到赠书后,发现书中介绍作者时,称其为“诗人思想者”。明显的过甚其词,就当是邵先生的一种期许吧。
初识邵先生,是在一九九四年夏秋之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范希文先生组织的泰山笔会上。那时,邵先生似乎开始谢顶,但还是满头黑发,回想起来真不禁令人感叹人生的迅忽。邵先生江南人,中等身材,略显瘦弱。
印象中,他穿的是平底布鞋,衣着朴素,态度谦和。当他和青年朋友在一起时,总是有说有笑,融洽无间。参加笔会的多是散文作家,关于散文写作,会间常有交流,还有专场讨论。平日,我很少单独找邵先生交谈,大多在山行时随众一起聊天。一次到扇子崖,邵先生主动邀我合影,两人双手抓紧了背靠的一根粗大铁索,头上是险峰,脚下是万丈悬崖。大约他喜欢这背景,曾在书中使用过这张照片。拍完照,我们对站着谈了许久,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算是闲谈。
邵先生是健谈的,会场上却很少说话。和邵先生一同参加过几次笔会,每次都是如此。会上,讨论苏叶的散文,除了众女士,汪曾祺老先生说得最多,大家也乐于倾听他的意见。他赞扬了一通,接着说到缺点,主要是写得太“满”,意思是不够含蓄,少了余韵,还拿国画的“留白”做比喻。我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审美这事情不能划一,可以不满,但也不妨满,接着又拿了油画和国画做比较,支持自己的观点。说完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场内一下子沉寂下来。看了看邵先生,他只是微笑着,跟大家一样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