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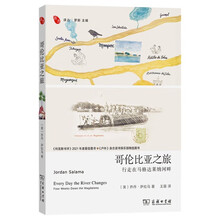




耶鲁大学中文教师、旅美作家苏炜的散文名篇自选集,题材选取宽泛,时空跨越度大,涉及自我成长、社会变迁、异域生活、文化洗礼、师友行状、亲情世态等,文字充满诗韵、哲趣而不失张力,富有文化内涵和文学气韵,充分在去国怀乡的过程中贯通中西。
辑三
春风一纸
雪浪琴缘
云根一脉泉飞落,琴上飙流碧玉珂。
律细弓深分月影,韵长弦重断沧波。
浩茫沉戟东吴水,高峻悲觞燕赵歌。
过尽千帆闲放眼,秋涛雪浪举青螺。
这是我为耶鲁青年大提琴家潘畅的演奏,以及为他手上那把新琴的命名,写下的一首旧体诗。2016年2月某日午后,下了课就忙着携妻会友,顶着滂沱大雨驱车前往纽约,为的是出席耶鲁音乐学院在卡内基音乐厅专门为潘畅举办的独奏音乐会。很凑巧,这天恰好是我的生日。仿佛是上天特意为我安排的一个别致的生日庆典,一想到这不光是潘畅音乐人生中迄今最重要的一场“Debut”(献演),更是他手上这把新琴面世后的首次正式亮相,又听闻制琴师还要专程为此千里迢迢从西雅图赶过来,众缘聚喜,千水汇流,就不禁让人为此生出许多遐想了。
“……我,我还能怎么办呢?”年前,多次为琴事碰壁之后,潘畅常常在我面前蹙眉犯难,我也一时为之语塞——琴,琴,琴。对于一位年轻的弦乐手,也许没有什么是比拥有或失去一把好琴更大更要命的事情了!
潘畅——二十郎当岁的川蜀伢子,挺拔个头,面容素净,耶鲁音乐学院一位近年崛起的大提琴新秀。因为担任我的中文助教而结缘,我则被他的弦刀入骨般的大提琴演奏一再震颤心魂,从此结为忘年莫逆。过去这些年间,潘畅手头拉得顺手的一把旧琴——可能是把苏联琴,大概是“文革”抄家的遗物,潘畅孩童时代的老师从旧货摊上以极低价购得,借给他学琴使用多年。不料此琴经潘畅经年的抚弄调理,伴随着他琴艺的成长,竟越拉越出光彩,从音质、音色到音量,都一显奇幻魅力。我在耶鲁音乐厅几次被潘畅的琴声打动,那些巨微俱现、远远超越潘畅年龄的仿佛沧桑历尽的琴声,就是从这把不起眼的“山野琴”上发出来的。潘畅拉琴走心。一阕格里格的奏鸣曲,他可以拉得宏大处惊天地泣鬼神而细微处丝丝缕缕揪人肺腑,震颤心魂。以致一场学院的“午饭室内乐”表演,他一曲拉罢却下不了台,被观众的掌声鼓噪一再唤出,不停地谢幕。耶鲁音院的各位行家宗师们,似乎也在一夜之间,发现了这块璞玉——讶异于藏在潘畅这个来自中国西南的大男孩羞涩、木讷的外表下,那个非凡的弦乐之灵。他的每一次演出都是那样弦深韵重,浑然天成,令人刮目相看。随之,一个个多少音乐人或许毕其一生之力都未必能获得的绝佳机会,似乎毫不费力地,落到潘畅身上了——
当年年底,他被盛邀到广州星海音乐厅,担任专为大提琴大师马友友新创制的大型大提琴与笙协奏曲《度》(写唐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的独奏,他的精彩演出受到了在场的著名指挥家余隆的盛赞并许以厚望。在成功举行完他的毕业独奏音乐会后,他的耶鲁业师——被誉为“大提琴界祖师爷”的九十六岁的一代宗师奥多·帕里索特(Aldo Parisot)先生,又推荐他在校外为当地社区开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他本该随即就毕业离校了,在他并未申请的情况下,音院院方破例决定:把潘畅留下,以全额奖学金让他再在耶鲁延读一年。显然,校方是下决心,把潘畅作为另一个未来的“马友友”加以精心栽培、额外加持了。不独此也,随即,一个个惊人的好消息接踵而来——已经有数十年传统的耶鲁年度大提琴专题音乐会,2015年的盛会,潘畅被选为唯一一位担任独奏的学生;而下一年度的耶鲁音院开学典礼,仅有的一个大提琴独奏曲目,也将由潘畅担任。院方还决定:请潘畅作为耶鲁音院优秀学生的代表,2015年12月末在纽约某业界沙龙乐厅,为一位乐界尊崇的百岁音乐人举办一场祝寿独奏音乐会;随后,2016年2月,将由耶鲁音乐学院挑头主办,在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为潘畅举办一场独奏音乐会——据闻,这已是耶鲁音院若干年来久未为单个学生做过的惊人举动了!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派鲜衣怒马、烈火烹油的意气风发之中,潘畅,却骤然遭遇到他音乐人生中的一道大坎儿。
——琴,琴,琴!2015年秋季开学,刚从成都探亲回来,出现在我面前的潘畅,满脸的疲惫憔悴,完全像一个失了魂的孩子。他哭丧着脸告诉我:他手上那把已被他拉得出神入化的大提琴,没有了,不见了——被他那位孩童时代的老师收走了,拿回去了!据说,因为有人看中潘畅所拉之琴的异质异彩,想出价几百万元购之,老师听闻之后,二话不说,就将这把借给潘畅使用多年、他本来从未“正眼看过”的“山野琴”要了回去——可谓:有借有还,再借却难;滴水不漏,理所当然!